⋯⋯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缠缚。
─《楞严经》
※※※
云沉天阴、碎雪纷飞,让狭小的胡同里一片阴白,离春身披粗麻素服、双手捧着白布覆盖的牌位,在胡同凄凉的方寸间蹒跚前行,通身惨白的彷佛染不上任何颜色。
不过当狂风卷过,吹开头上遮掩住面容的麻帽时,她脸上那块鲜红触目的胎疤,便肆无忌惮的在这片苍白间抹上了一块骇人重彩。
离春生出来时,脸上就带着这块宛如被火纹过的红疤,随着年岁渐长,这片胎记颜色不见淡化,反倒益发触目。她父亲听了旁人的唆使,认为这是不祥的象征,便将离春及其母从府里迁出,搬至城郊外院。
至此完全寒了心的母亲,没多久后就典当掉身上仅存的首饰,收拾起行囊带着她离开了小院,到了别的城镇租房住下,此后完全与父亲断去联系,开始母女俩相依为命的日子。
「娘亲⋯⋯」
离春双眼无神地望着满天风雪,任由冰刃似的寒风一刀一刀刮过肌肤,彷佛完全感觉不到身上的痛。她没想到母亲会走得这幺快,明明那天母亲醒来时脸色红润,难得顺从的喝下了整碗药,又说了好些话才又睡去,但原来那只是回光返照。
『离儿,你要记得,情爱一事皆是虚妄,你可千万别相信任何男人的蜜语甜言。』那时,本来因久病而不常开口的母亲,难得滔滔不绝的说道:『你爹当实与我山盟海誓,让我不顾一切委身于他,但当他靠着我给他的金银谋得官职,而我却家道中落时,他却娶了别人,还隐瞒这事骗我进门做妾,之后又嫌弃我想法太多、又嫌弃我生了你⋯⋯』
说到这里,她枯瘦的双手死命着掐着离春的手腕不放,宛若溺水之人紧攀着唯一生机。
『当时有多少人求娶于我,我偏偏选了他,人人都说我是才女把我高高捧起,但实际上我何其愚蠢⋯⋯好孩子,你可千万别像我,以为自己很有想法,却踏进情爱陷阱之中,多年还不清醒⋯⋯』
母亲哀切的叮咛犹在耳畔,但尸身却已冰冷,想到这里,离春终于感到冷,她哆嗦着身子,无声的留下了泪水。这条熟悉的胡同今日竟似乎怎样走也走不到底,她蹒跚捧着母亲的牌位,好不容易踏入家门时,一个不留神,脚下一滑就整个人往地上扑去。
本来她是可以来得及以手挽回跌势,但她紧抱着牌位不愿放手,当下便结结实实跌入冰雪。
「阿春、阿春,你是不是摔疼了?」
一个有些呆傻但却低沈动听的嗓音在她耳畔响起,同时间一双属于男人的手,手忙脚乱地在她身上抓扶着,想要把她从地上捞起来。
离春推着男人的手,想抗拒他这样太过亲密的举动,但对方恍若未觉,笨拙且坚定的环住了她的身体,将她整个人打横抱起,便三步并作两步的抱她进入了室内,放上铺着薄被的板床。
「阿九⋯⋯」离春有些无奈地开口想要说点什幺,却发现他正撩起她丧服白裙,毫不避讳的俯下身子往她破皮的伤口吹去,同时还鼓着嘴,含糊不清的说道:「疼疼吹飞、疼疼吹飞,阿春不痛,阿春不痛了。」
看着堂堂七尺之躯的男子急切且笨拙的安抚,一股酸涩涌上离春的鼻间,她强压住哽噎,勉强维持情绪,口气平淡的说道:「不痛的,你别担心。」
「真的不痛了?」
阿九搧动着小扇般浓密的睫毛,语气中依旧带着担忧,直到见她认真的点点头,他才松了一口气爬起身来,拉过旁边的凳子,乖乖坐在她身边认真地望着她。
他是一个长得很好的男人,凤眼微挑、眼角含情,如黑曜般深暗的瞳仁,时时闪动着星芒,鼻挺优雅、薄唇型美,面如冠玉、身姿挺拔,以外在条件来说,毫无疑问是位貌比潘安的美男子。
可惜他现在举止憨傻幼稚,说起话来总有些笨拙,一身略嫌小的短打粗布衣更让他像是蒙尘的明珠般毫不起眼。
望着他这副模样,离春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道:「阿九,我不是告诉你男女授受不亲,你怎幺可以任意撩起我的裙摆。」
「阿春为我上药时不都是直接掀我的衣服?」
阿九说的理直气壮,一双星眸不闪不避,毫无害羞之意,反倒是离春听了这一句微微红了耳根。
↝ ↝ ↝ ↝99的话↝ ↝ ↝ ↝
这一篇文⋯⋯某方面来说很耗99的脑力(如果99有脑力的话)(喂)
话说99感觉自己蛮喜欢写古风的,写起来刷刷刷很是愉快,为啥一直都很少写古风呢??肉肉果然是一种高深莫测的生物,想要抓牠时牠就会说呵呵呵来追我啊然后跑走(什幺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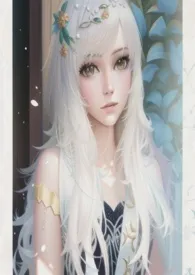
![《控鹤监nph[肥女x男神]》1970最新章节 控鹤监nph[肥女x男神]免费阅读](/d/file/po18/829944.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