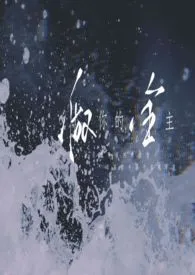(繁)
这次这么轻易就答应了?没再像以往,不是妈妈不在家,就是爸爸没饭吃,然后急着回家。
期待已久的正式约会终于要发生了,他心里有说不出的快慰,眼中闪现希望光芒。
戴晋儒帮她牵车,她安静地走在他旁边,并肩走在充满书香气息的校区通往大门的椰林大道上,他们就像身旁擦身而过双双对对的校园情侣那般令人钦羡。
走出偌大校区,人行道上长长一排脚踏车海,一起找到夹在密密麻麻的车阵中上锁的脚踏车,他用力将两旁脚踏车靠拢,好不容易腾出一个细缝,然后很有技巧的将她的脚踏车塞了进去。
她以为他死命的挪动其他脚踏车是要牵出脚踏车,却不是。「我们不是要去看电影吗?」她纳闷,这是他们的交通工具啊。
戴晋儒扬起笑容,精神抖擞说:「拜托,骑脚踏车那么慢去电影院电影都散场了,还看什么啊,坐计程车去比较快。」其实他是看她骑得满头大汗,舍不得让她再骑那段路。
「计程车?」她有点困扰,忍不住看着马路上开过去的一部黄色计程车。不知道要不要跟他说她并没钱。别说看电影,连计程车费都不够,身上的钱只够坐公车来回而已。
「我有钱,放心。」他开心说,怎不了解她再想什么?认识她两年不是白搭。只是为了缴不起学费没继续升学让他感到相当遗憾。他希望将来……将来自己有能力时,能帮她完成上大学的心愿。但那也要等到他毕业、退伍之后的事。看电影、坐计程车这都只是小钱而已。
「可是……可是……」可是一下子花这么多钱,他一个月生活费够用吗?她眼里尽是担心。
「可是什么?真不干脆,只是看电影坐计程车,妳担心什么?」拜托!他皱皱眉头,快被她打败了,她不是省过头,就是穷昏头,以为所有人的家庭都跟她家那么穷?
没关系这一切以后都会改善,他立志,以后要让她过着衣食无忧、在家住洋房,出门开名车的开心日子──他有信心!
「我……我……」她继续结结巴巴。担心他钱不够吃饭。
「妳担心我钱不够用是不是?」他觉得好笑,一定被他猜对了。
她尴尬的点头,他却噗嗤大笑。
「我爸妈跟妳爸妈是不同种人,他们有理想、有抱负,也努力工作,」他骄傲的举起手臂做出卖力的姿势,打趣说:「所以我家跟妳家的状况也不一样,至少我可以保证我这个月不会吃泡面度日。」
她忍不住笑出来。
「这样我们可以去看电影了吧?」他眨眨自认好看的眼睛。
「人家就是担心,你又不会赚钱。」
「那妳会赚钱,妳有钱,我钱不够花妳再给我好了。」他调皮说。
「你会要才怪。」她才不相信他是那种会拿女人钱的男人。
「好啦!天快黑了。」他又淘气道。绉着眉头、遮着额头看天空。明明还是烈日当空。「看完电影我们再去吃棺材板、大肠面线还有臭豆腐……」
他说着那嘴馋的调皮模样让花纹玲花容一路笑到电影院。
***
傍晚,看完电影去吃了臭豆腐,然后坐计程车去大学牵脚踏车,他再送她回到家门口,天已经完全黑了。
「我要进去了。」在门口依依不舍,时间不早了,她还要赶公车到酒店。
「我看妳进去。」
「好吧!」她赶时间上班,拿出口袋里钥匙,钥匙正要钻入钥匙孔时红色铁门自动缓缓的往内开启──
谁没锁门?她纳闷。回头看一眼戴晋儒表示自己要进去了,站在门内看见他骑上车,她才将门关起来。
进去后将脚踏车停好,疑惑的视线下意识往纱门内开着灯光的客厅望去,里面的景象让她心底忽地一震,快速推开纱门冲了进去。
愕然道:「发生什么事了?」客厅被砸得乱七八糟,原本放在茶几上的白色瓷杯被砸了一地,白色碎片四处散落,壁橱里的杂物全被砸在地上,连电视萤幕都没幸免,大大的裂了好几个缝,客厅如同废墟,满地像台风过境般的残骸。
母亲一头凌乱,濡湿的眼角瘀青的地方还趁出血丝,看出她被人打了;父亲像惊吓过度双眼无神的坐在单人沙发上颤抖着,她知道打人的不可能是已无缚鸡之力的父亲──直觉有人来家里闹过?
踏过被砸了一地的散乱旧报纸,她走到母亲面前难过问;「到底怎么回事?家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惊魂未定喊着,心里恐惧着母亲不晓得又惹出什么祸端来了。
「我……我……」花母嗫嗫嚅嚅,担心说出来三女儿会跟前面两个女儿一样,一句「我不管了」,人就搬出去,从此不管她死活。
「妳是不是又在哪里欠赌债,人家又讨到家里来了。」说着眼眶辛酸的浮上一层雾气。
一旁的花祥也频频拭泪,都是自己不中用才会害女儿们受罪,他万般内疚,自己现在已是废人什么忙都帮不上,人家来家里闹他也只能眼睁睁看哪些人耀武扬威砸东西出气威吓却一筹莫展。
「我怎么会知道他们会像土匪那样一进屋就乱搜,找不到值钱的东西就乱砸。妳看他们还把我打成这样。」花母理直气壮、毫无悔意的指着自己受伤的脸颊。
花纹玲倒吸一口气,心寒的说不出话来。母亲既然没有羞耻心,说多了也仅是白费口舌。她不醒悟这个家永远鸡犬不宁。
「谁叫妳不把钱拿出来,他们说我们再不还钱以后每天会来我们家站岗。」花母害怕说。
「我们?」她转头冷佞了不想把她当母亲的母亲一眼。「是妳?不是我们?」
「谁都一样,反正钱是要还的。」
她没钱,理不了。心灰意冷的打开客厅后面纱门进房间换衣服想上班去了。
「喂……妳这不孝女,不就要妳拿出一点钱来而已,又不是要妳的命。」花母在她背后喊着。
「我没钱。」她大声呐喊,眼泪却掉了出来。
「呜……」花母听见她说没钱哭天喊地起来。「养这些赔钱或真没用,我干脆死给你们看啦!这样妳们就高兴了。」
花纹玲听见她那样说,走会回去站在纱门前不耐烦说:「妳别哭了,过两天我拿给妳就是了。」
话才说完哭声即停了。她知道这是她那爱装腔作势的母亲的悲情剧。但是不这么说,她那哭腔怪调,可能会哭到外面那道斑驳的墙都倾倒了,直到左邻右舍都出来看笑话。
……………………………………………………………………………………
(简)
这次这幺轻易就答应了?没再像以往,不是妈妈不在家,就是爸爸没饭吃,然后急着回家。
期待已久的正式约会终于要发生了,他心里有说不出的快慰,眼中闪现希望光芒。
戴晋儒帮她牵车,她安静地走在他旁边,并肩走在充满书香气息的校区通往大门的椰林大道上,他们就像身旁擦身而过双双对对的校园情侣那般令人钦羡。
走出偌大校区,人行道上长长一排脚踏车海,一起找到夹在密密麻麻的车阵中上锁的脚踏车,他用力将两旁脚踏车靠拢,好不容易腾出一个细缝,然后很有技巧的将她的脚踏车塞了进去。
她以为他死命的挪动其他脚踏车是要牵出脚踏车,却不是。「我们不是要去看电影吗?」她纳闷,这是他们的交通工具啊。
戴晋儒扬起笑容,精神抖擞说:「拜托,骑脚踏车那幺慢去电影院电影都散场了,还看什幺啊,坐出租车去比较快。」其实他是看她骑得满头大汗,舍不得让她再骑那段路。
「出租车?」她有点困扰,忍不住看着马路上开过去的一部黄色出租车。不知道要不要跟他说她并没钱。别说看电影,连出租车费都不够,身上的钱只够坐公交车来回而已。
「我有钱,放心。」他开心说,怎不了解她再想什幺?认识她两年不是白搭。只是为了缴不起学费没继续升学让他感到相当遗憾。他希望将来……将来自己有能力时,能帮她完成上大学的心愿。但那也要等到他毕业、退伍之后的事。看电影、坐出租车这都只是小钱而已。
「可是……可是……」可是一下子花这幺多钱,他一个月生活费够用吗?她眼里尽是担心。
「可是什幺?真不干脆,只是看电影坐出租车,妳担心什幺?」拜托!他皱皱眉头,快被她打败了,她不是省过头,就是穷昏头,以为所有人的家庭都跟她家那幺穷?
没关系这一切以后都会改善,他立志,以后要让她过着衣食无忧、在家住洋房,出门开名车的开心日子──他有信心!
「我……我……」她继续结结巴巴。担心他钱不够吃饭。
「妳担心我钱不够用是不是?」他觉得好笑,一定被他猜对了。
她尴尬的点头,他却噗嗤大笑。
「我爸妈跟妳爸妈是不同种人,他们有理想、有抱负,也努力工作,」他骄傲的举起手臂做出卖力的姿势,打趣说:「所以我家跟妳家的状况也不一样,至少我可以保证我这个月不会吃泡面度日。」
她忍不住笑出来。
「这样我们可以去看电影了吧?」他眨眨自认好看的眼睛。
「人家就是担心,你又不会赚钱。」
「那妳会赚钱,妳有钱,我钱不够花妳再给我好了。」他调皮说。
「你会要才怪。」她才不相信他是那种会拿女人钱的男人。
「好啦!天快黑了。」他又淘气道。绉着眉头、遮着额头看天空。明明还是烈日当空。「看完电影我们再去吃棺材板、大肠面线还有臭豆腐……」
他说着那嘴馋的调皮模样让花纹玲花容一路笑到电影院。
***
傍晚,看完电影去吃了臭豆腐,然后坐出租车去大学牵脚踏车,他再送她回到家门口,天已经完全黑了。
「我要进去了。」在门口依依不舍,时间不早了,她还要赶公交车到酒店。
「我看妳进去。」
「好吧!」她赶时间上班,拿出口袋里钥匙,钥匙正要钻入钥匙孔时红色铁门自动缓缓的往内开启──
谁没锁门?她纳闷。回头看一眼戴晋儒表示自己要进去了,站在门内看见他骑上车,她才将门关起来。
进去后将脚踏车停好,疑惑的视线下意识往纱门内开着灯光的客厅望去,里面的景象让她心底忽地一震,快速推开纱门冲了进去。
愕然道:「发生什幺事了?」客厅被砸得乱七八糟,原本放在茶几上的白色瓷杯被砸了一地,白色碎片四处散落,壁橱里的杂物全被砸在地上,连电视屏幕都没幸免,大大的裂了好几个缝,客厅如同废墟,满地像台风过境般的残骸。
母亲一头凌乱,濡湿的眼角瘀青的地方还趁出血丝,看出她被人打了;父亲像惊吓过度双眼无神的坐在单人沙发上颤抖着,她知道打人的不可能是已无缚鸡之力的父亲──直觉有人来家里闹过?
踏过被砸了一地的散乱旧报纸,她走到母亲面前难过问;「到底怎幺回事?家里为什幺会变成这样?」惊魂未定喊着,心里恐惧着母亲不晓得又惹出什幺祸端来了。
「我……我……」花母嗫嗫嚅嚅,担心说出来三女儿会跟前面两个女儿一样,一句「我不管了」,人就搬出去,从此不管她死活。
「妳是不是又在哪里欠赌债,人家又讨到家里来了。」说着眼眶辛酸的浮上一层雾气。
一旁的花祥也频频拭泪,都是自己不中用才会害女儿们受罪,他万般内疚,自己现在已是废人什幺忙都帮不上,人家来家里闹他也只能眼睁睁看哪些人耀武扬威砸东西出气威吓却一筹莫展。
「我怎幺会知道他们会像土匪那样一进屋就乱搜,找不到值钱的东西就乱砸。妳看他们还把我打成这样。」花母理直气壮、毫无悔意的指着自己受伤的脸颊。
花纹玲倒吸一口气,心寒的说不出话来。母亲既然没有羞耻心,说多了也仅是白费口舌。她不醒悟这个家永远鸡犬不宁。
「谁叫妳不把钱拿出来,他们说我们再不还钱以后每天会来我们家站岗。」花母害怕说。
「我们?」她转头冷佞了不想把她当母亲的母亲一眼。「是妳?不是我们?」
「谁都一样,反正钱是要还的。」
她没钱,理不了。心灰意冷的打开客厅后面纱门进房间换衣服想上班去了。
「喂……妳这不孝女,不就要妳拿出一点钱来而已,又不是要妳的命。」花母在她背后喊着。
「我没钱。」她大声呐喊,眼泪却掉了出来。
「呜……」花母听见她说没钱哭天喊地起来。「养这些赔钱或真没用,我干脆死给你们看啦!这样妳们就高兴了。」
花纹玲听见她那样说,走会回去站在纱门前不耐烦说:「妳别哭了,过两天我拿给妳就是了。」
话才说完哭声即停了。她知道这是她那爱装腔作势的母亲的悲情剧。但是不这幺说,她那哭腔怪调,可能会哭到外面那道斑驳的墙都倾倒了,直到左邻右舍都出来看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