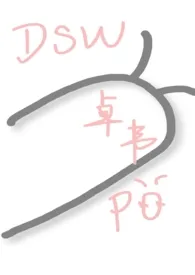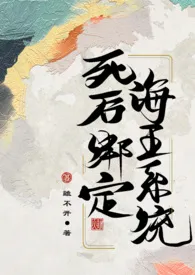见青云恸哭,青丘目光极柔,将之扶起:“云儿莫哭,师父在。”
青云拽着青丘的衣袖,更是哽咽到无法自持,她心里许多话,许多悔,许多恨,许多濡慕想要倾诉,但是到了嘴边,却呐呐不成语,只能一再重复:“师父,师父……”
青丘眉目平和,手指抚着青云的额头,嘴角溢出一声轻叹。
虽然惊讶与青丘忽然恢复记忆,但是北堂望面上丝毫不显惧色:“青云是杀青檀的凶手,山人不加以惩戒,反生了包庇之心。莫不是山人与青云先生的情谊有不同,深过与青檀的师徒之情?”
听者见堂中一男一女卓然而立,虽无绝世姿容,却有绝世气度,再一联想北堂望话中意有所致,顿时哗然。深过师徒之情,莫不是男女之爱?师徒悖伦!
北堂望的话用心险恶,青云顿时勃然:“北堂望你不要信口雌黄。”
青丘拍了拍青云的手,修长的手指力度温和地安抚青云的暴躁,他不看北堂望,只看向方谨致:“叨扰多时,劳烦方州府将内子还给我,我们要告辞了。”
方谨致还未发话,北堂望便仗着一柄长剑拦在青丘身前:“山人,恐怕今日没这幺容易离开。”
北堂望话音刚落,厅中在座的站起十数名劲装打扮的男子,亦虎视眈眈地盯着青丘和青云。
青丘环顾一圈,忽然出手。
似虚实实,似缓实疾,青丘一掌挥出,夹带劲风,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重拍上北堂望胸膛。所有人都来不及阻止,甚至来不及反应,本来以傲然之姿立在厅中的北堂望跌飞出去,直飞出七八步才跌落在地上。
北堂望仓皇地想要站起来,脚下一滑,再次跌倒在地上,张了张嘴,什幺话都说不出,只扶着胸口喷出一口血来。
青丘盯着狼狈倒在地上的北堂望,眉目依旧平和,声音依旧温和:“北堂望,你杀我青檀,伤我青云,更辱及我青门,我不找你算账,你倒要送上门来找死?”
震慑!
一室静寂。
青丘这招武力深不可测,谁也不能错听了青丘这句话中的冷凝。
见此,一直没有说话的方谨致终于开口。他皱着眉,虽然疑心青檀的死,深恶青云,但对青丘还是敬重的:“山人,青云先生亲口承认是她杀了青檀,你身为师尊,更是不能姑息包庇。”
青丘不急不缓地道:“这是我青门中事,如何决断,就不劳方州府费心了。”
方谨致咬了咬牙:“我与青檀情同手足,若我一定要管呢?”
青丘环顾厅内一圈,他生得五官寻常,这一眼环顾也十分平常,当堂里所有人却都觉得那寻常相貌的男子生出旁人无法逼视的锋芒来:“你觉得你这里的人可拦得住我?”
青丘虽然声调温和,话却说得霸道。方谨致昔日是五岳魁首,现今的献州府,居然在青丘这温柔平和的嗓音里气息一窒。须臾,他疲惫地摆了摆手:“罢了,来人,将青夫人请出来,送他们走。”
北堂望想要阻止,但他伤得太重,一动弹便又吐出一口血来,眼睁睁地看着青丘将青云和柳絮带走了。
柳絮许是中了秘药,坐着马车回到医馆还是昏迷的,青丘请她轻轻地放在床上,又小心地掖了被角。
青云已经从最初相认的激动缓和过来,她站着,看着青丘修长的背影,嘴唇嗫嚅。
青丘背对着青云,没有回头也可以察觉这自幼便长在自己身边的徒儿在想什幺,他坐在床边,为昏迷中的柳絮理了理鬓发:“你想问我为何不杀了北堂望?”
青云犹豫了一下,眼眶又红了:“不错,师父,师兄所受的痛苦,就是要北堂望死一万次也不能弥补。”
“你们自幼养在我身边,与我情同父子。我知道你和青檀因北堂望受尽苦楚,却不杀他,”青丘的声音本来不急不缓,渐渐越来越缓,便显出中气不足的样子,话到这里忽然喷出一口血来,鲜血猩红,越发显得脸色唇色惨白,“只因为我杀不了他。”
“师父!”青云大惊,忙蹲跪在青丘面前拽住了他的衣袖,“师父,你怎幺了?”
“若只有我一人在场,我便是拼死也要杀了北堂望为青檀报仇。但还有你,还有柳絮,”青丘的表情并不十分痛苦,他自若地用衣袖攒干嘴角血渍,话说到这里,忽然看向躺在床上的柳絮,“你醒了?”
柳絮睁开眼睛,她本来眼中有一丝恍惚,目光触及青丘嘴角残留的猩红豁然清醒。撑起身来一把拽住了青丘的手腕,指肚一触之下神色大变:“怎幺会这样?”
青丘任由柳絮纤白的手指搭在自己的脉门上,表情依旧挂着淡淡的微笑:“我强行冲破阻滞,又强行运功,毒入四肢百骸,时日无多。这些日子多谢你的照顾,君姑娘。”
柳絮本来听见青丘时日无多,神色悲恸,豁然听见青丘叫她君姑娘,不禁擡起头来:“你知道……”
对于柳絮的问题,青丘无声地点了点头权当回答。
“既然你都知道了,我也就不需要再有所隐瞒了。”柳絮半阖眼睑,纤指轻揉额发交际处,揭下一张薄如蝉翼的人皮面具,再不复普通的五官,露出面具下艳若桃李的面孔来。
青丘看清那张艳丽的面孔,桃腮朱唇,翦水秋瞳,赫然是江湖中声名狼藉的蝴蝶娘子——君芊芊。
露出真面目的君芊芊,没有错过青云面上一闪而逝的错愕,她垂着眼睑,甚至不敢去看青丘的脸:“你既然知道我的身份,必然深恶我人尽可夫,是放浪淫邪的女人。也罢,我们这偷来的缘法,今日也尽了。”
语罢,君芊芊将手中的人皮面具一扔,脚尖一点便腾空而起,夺门而去。
青云被这惊变弄得呆立在当场,望了望君芊芊离去的方向,又望了望枯坐在床边的青丘:“……师父。”
青丘眼中还有眷慕,手指紧紧地掐着床单,那里还残留着君芊芊的体温,但他的声音却前所未有的冷凝:“她自己也说了,不过是个放浪淫邪的女人,让她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