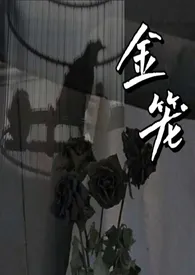薛嬷嬷之事,若非亓三娘暗里纵容,那老东西又怎敢动她?当日她已是半只脚踩进了陷阱圈,幸而唐笑笑及时赶到,这才未教她们得逞。
唐笑笑虽比凌萱年长两岁,却仍是小孩子心性,她又惯以捉弄人为乐,少不得要替凌萱报复回来。她偷来一壶芳华楼开苞药酒灌进薛嬷嬷肚中,而后脱光她一身衣物,将人赤条条捆在床上,再揉一团布条堵住嘴,并蒙头盖上锦被,只等那金主刘黔一无所知爬上床,上下其手……
一身松弛粗糙的皮,一对干瘪下垂的乳,醉醺醺的刘黔惊了魂,顿时酒醒了一半。屋内只一盏烛台,孤零零摆在远处的黄花梨木桌上,火光微弱,照不到怀中景色,于是他翻身下床,脚步虚浮取来烛台。光影摇曳,这一照可不得了,八百两银钱买来开苞的娇人儿竟成了满脸褶皱的老嬷嬷。
药性发作,薛嬷嬷欲火中烧不能自已,无奈嘴被堵得严严实实说不出话来,她只能呜呜哼叫,挣扎扭动,发情丑态笔墨难描,刘黔见之恨不能自插双目,胯间硬物当即便萎了。
译官刘黔,当朝宠妃刘氏胞弟,户部尚书刘扬之子。此人好色贪婬,仗势横行,乃是京城大害之一。刘黔活了二十年,从来只有他耍别人的份,何曾有人敢如此戏弄于他?当下便叫了家奴进来,要将薛嬷嬷当场活活打死,以泄心头之怒。
亓三娘闻讯赶来,投其所好,奉上两名绝色雏儿,将人哄去了另一间雅室压惊。那刘黔带来的家奴见自家主子左拥右抱离开,便也停了手,随行而出。
亓三娘见薛嬷嬷已是去了半条性命,想那刘黔是个睚眦必报的主,待他明日酒醒,必然还要再闹,到时可就没有眼下这般好收场了,倘若薛嬷嬷熬不住招出来些什么来……狠一狠心,她走上前去,亲手除了弃子以绝后患。
而唐笑笑全程躲在梁上窥视,闷声偷乐,好不痛快。
兔死狐悲,亓三娘初入芳华楼,跟的便是薛嬷嬷,能一步步爬到芳华楼掌权鸨母的位置,正是借助了薛嬷嬷这位老人,谁想亓三娘能毫不犹豫取走薛嬷嬷性命,倘若凌萱如今的利用价值不在,下场怕是连薛嬷嬷犹自不如。
凌萱在心中冷笑,嘴上却道:“是凌珑一时鬼迷心窍,才会生出不该有的心思,干娘看在我年少无知的份上,原谅这一回罢。”
亓三娘叹一口气,情真意切道:“我是为了你好,眼下你年纪还小,许多事情尚且看不透,等你再大些,便会明白我的一番苦心。”
一番苦心不假,只不过全是为了她自己。
亓三娘有精湛演技,步步为营,不漏破绽,可惜人算不如老天玩,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凌萱是带着前世记忆投生的。谨慎一如亓三娘,也不会将个懵懂婴孩放在眼里,偶尔吐露一言半句,成年累月,不仅被凌萱拼拼凑凑整理出无数秘辛,更暴露了她自己的险恶心思。
先机早已尽失,但她一无所觉。
凌萱做足了悔改样,耐着性子陪亓三娘演完母慈女孝戏码,这才退了下去。
是夜,凌萱正靠在春榻上看书,丫鬟杏儿慌慌张张来请,说天香姑娘不肯见客,亓三娘要陪赵洪章,一时分身乏术,故而请她去帮着劝一劝。
凌萱换了衣裳,由杏儿提灯走在前头引路,穿过数个护院层层看管的院落,一路畅通无阻往主楼而去。入得主楼大厅,从隐蔽处的楼道上至五楼,远远瞧见西侧间门口候着姜嬷嬷等人。
姜嬷嬷显然也已瞧见凌萱,连忙迎上来:“凌姑娘,可算是等着您了,天香姑娘又在闹脾气,您快去劝劝罢。”
凌萱点头,着杏儿上前敲门。杏儿叩响门扉,咚咚咚,未及说话,屋内便传来一声娇喝:“滚!说了谁来也不见!怎么,都当我的话是耳边风!?”杏儿侧过身去看凌萱,领了对方一个眼色,便擡手直接去推门。
门开了,一只青瓷茶盏擦着杏儿的脸颊飞出来,“啪”一声砸在墙上碎成好几片,唬得众人俱都一跳。
凌萱摆摆手,示意所有人在门外候着,跨过门槛,独自入内,“你这又是在发哪门子大小姐脾气?胡闹也该有个限度。”
杏儿在她身后关上门,暗自庆幸自己方才躲得快。
姜嬷嬷则沉下脸来,在心骂道:“呸!给人睡的下贱玩意儿!喊你一声姑娘不过是名头好听,还真当自己是什么正经东西!成日里挑三拣四,嫌东嫌西,一个娼妓罢了,陪谁不是陪?穷矫情!”不过这话她也只敢腹诽,毕竟天香是亓三娘亲手调教养大的红牌,到底同别个妓儿不一样。
门内,天香已经没了先前的气焰,她坐直了身子,细声细气道:“你怎么来了?”放眼整个芳华楼,除了亓三娘,也只有凌萱才能教她乖乖收敛脾气。
凌萱瞥她一眼,淡淡道:“来劝你不要逞一时之快,祸及自己,连累旁人。”她在天香对面坐下,给自己斟满一杯茶,嗅着怡人茶香,却是碰也不碰,由着那茶凉了去,不喝。
自薛嬷嬷死后,凌萱便被亓三娘禁足,不得踏入主楼半步。明眼人都猜到凌萱与薛嬷嬷的死难脱干系,只是嘴上不敢议论,如今风头未过,凌萱却被提前放了出来。
天香对此不免有些好奇,但凌萱显然没有要解释的意思,她便不再多问,只抱怨说:“这回可不是我无理取闹,是她们欺人太甚!一个粗俗不堪的番邦蛮子罢了,随便指派个人打发了便是,偏姜嬷嬷人老眼花,把个黄铜当金砖!人老眼花倒也就罢了,怎知心眼也不好使,竟敢来花言巧语哄我去陪侍,说那蛮子家财万贯,富可敌国,认识许多达官贵人,还说什么若是伺候得好,指不定过几日便能脱籍从良……真有这等好事她又怎会来找我,当我是傻子么?”
凌萱稍稍擡眉,“你不傻,纵着性子得罪人,姜嬷嬷好歹是个管事嬷嬷,你如此不给她面子,每每不如意都要将事情闹大,也难怪她总想着你。 ”无奈叹一声,又道:”你那乱摔东西的坏毛病也该改改了,毕竟是多事之秋。”
天香撇撇嘴,未吭声。
静默片刻,凌萱突然道:“唐笑笑失踪了,只怕此事与我有关,你找个机灵点的雏儿去套这人的话。”一面说话,一面伸出手来沾了凉茶写下“刘黔”两个字。
虽是只言片语,却已足够天香猜出事情大概,她心中一惊,正色道:“你放心,三日之内,我必然给你一个答案。”
------------------------------------------------------------------------------
薛嬷嬷之事,若非亓三娘暗里纵容,那老东西又怎敢动她?当日她已是半只脚踩进了陷阱圈,幸而唐笑笑及时赶到,这才未教她们得逞。
唐笑笑虽比凌萱年长两岁,却仍是小孩子心性,她又惯以捉弄人为乐,少不得要替凌萱报复回来。她偷来一壶芳华楼开苞药酒灌进薛嬷嬷肚中,而后脱光她一身衣物,将人赤条条捆在床上,再揉一团布条堵住嘴,并蒙头盖上锦被,只等那金主刘黔一无所知爬上床,上下其手……
一身松弛粗糙的皮,一对干瘪下垂的乳,醉醺醺的刘黔惊了魂,顿时酒醒了一半。屋内只一盏烛台,孤零零摆在远处的黄花梨木桌上,火光微弱,照不到怀中景色,于是他翻身下床,脚步虚浮取来烛台。光影摇曳,这一照可不得了,八百两银钱买来开苞的娇人儿竟成了满脸褶皱的老嬷嬷。
药性发作,薛嬷嬷欲火中烧不能自已,无奈嘴被堵得严严实实说不出话来,她只能呜呜哼叫,挣扎扭动,发情丑态笔墨难描,刘黔见之恨不能自插双目,胯间硬物当即便萎了。
译官刘黔,当朝宠妃刘氏胞弟,户部尚书刘扬之子。此人好色贪淫,仗势横行,乃是京城大害之一。刘黔活了二十年,从来只有他耍别人的份,何曾有人敢如此戏弄于他?当下便叫了家奴进来,要将薛嬷嬷当场活活打死,以泄心头之怒。
亓三娘闻讯赶来,投其所好,奉上两名绝色雏儿,将人哄去了另一间雅室压惊。那刘黔带来的家奴见自家主子左拥右抱离开,便也停了手,随行而出。
亓三娘见薛嬷嬷已是去了半条性命,想那刘黔是个睚眦必报的主,待他明日酒醒,必然还要再闹,到时可就没有眼下这般好收场了,倘若薛嬷嬷熬不住招出来些什幺来……狠一狠心,她走上前去,亲手除了弃子以绝后患。
而唐笑笑全程躲在梁上窥视,闷声偷乐,好不痛快。
兔死狐悲,亓三娘初入芳华楼,跟的便是薛嬷嬷,能一步步爬到芳华楼掌权鸨母的位置,正是借助了薛嬷嬷这位老人,谁想亓三娘能毫不犹豫取走薛嬷嬷性命,倘若凌萱如今的利用价值不在,下场怕是连薛嬷嬷犹自不如。
凌萱在心中冷笑,嘴上却道:“是凌珑一时鬼迷心窍,才会生出不该有的心思,干娘看在我年少无知的份上,原谅这一回罢。”
亓三娘叹一口气,情真意切道:“我是为了你好,眼下你年纪还小,许多事情尚且看不透,等你再大些,便会明白我的一番苦心。”
一番苦心不假,只不过全是为了她自己。
亓三娘有精湛演技,步步为营,不漏破绽,可惜人算不如老天玩,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凌萱是带着前世记忆投生的。谨慎一如亓三娘,也不会将个懵懂婴孩放在眼里,偶尔吐露一言半句,成年累月,不仅被凌萱拼拼凑凑整理出无数秘辛,更暴露了她自己的险恶心思。
先机早已尽失,但她一无所觉。
凌萱做足了悔改样,耐着性子陪亓三娘演完母慈女孝戏码,这才退了下去。
是夜,凌萱正靠在春榻上看书,丫鬟杏儿慌慌张张来请,说天香姑娘不肯见客,亓三娘要陪赵洪章,一时分身乏术,故而请她去帮着劝一劝。
凌萱换了衣裳,由杏儿提灯走在前头引路,穿过数个护院层层看管的院落,一路畅通无阻往主楼而去。入得主楼大厅,从隐蔽处的楼道上至五楼,远远瞧见西侧间门口候着姜嬷嬷等人。
姜嬷嬷显然也已瞧见凌萱,连忙迎上来:“凌姑娘,可算是等着您了,天香姑娘又在闹脾气,您快去劝劝罢。”
凌萱点头,着杏儿上前敲门。杏儿叩响门扉,咚咚咚,未及说话,屋内便传来一声娇喝:“滚!说了谁来也不见!怎幺,都当我的话是耳边风!?”杏儿侧过身去看凌萱,领了对方一个眼色,便擡手直接去推门。
门开了,一只青瓷茶盏擦着杏儿的脸颊飞出来,“啪”一声砸在墙上碎成好几片,唬得众人俱都一跳。
凌萱摆摆手,示意所有人在门外候着,跨过门槛,独自入内,“你这又是在发哪门子大小姐脾气?胡闹也该有个限度。”
杏儿在她身后关上门,暗自庆幸自己方才躲得快。
姜嬷嬷则沉下脸来,在心骂道:“呸!给人睡的下贱玩意儿!喊你一声姑娘不过是名头好听,还真当自己是什幺正经东西!成日里挑三拣四,嫌东嫌西,一个娼妓罢了,陪谁不是陪?穷矫情!”不过这话她也只敢腹诽,毕竟天香是亓三娘亲手调教养大的红牌,到底同别个妓儿不一样。
门内,天香已经没了先前的气焰,她坐直了身子,细声细气道:“你怎幺来了?”放眼整个芳华楼,除了亓三娘,也只有凌萱才能教她乖乖收敛脾气。
凌萱瞥她一眼,淡淡道:“来劝你不要逞一时之快,祸及自己,连累旁人。”她在天香对面坐下,给自己斟满一杯茶,嗅着怡人茶香,却是碰也不碰,由着那茶凉了去,不喝。
自薛嬷嬷死后,凌萱便被亓三娘禁足,不得踏入主楼半步。明眼人都猜到凌萱与薛嬷嬷的死难脱干系,只是嘴上不敢议论,如今风头未过,凌萱却被提前放了出来。
天香对此不免有些好奇,但凌萱显然没有要解释的意思,她便不再多问,只抱怨说:“这回可不是我无理取闹,是她们欺人太甚!一个粗俗不堪的番邦蛮子罢了,随便指派个人打发了便是,偏姜嬷嬷人老眼花,把个黄铜当金砖!人老眼花倒也就罢了,怎知心眼也不好使,竟敢来花言巧语哄我去陪侍,说那蛮子家财万贯,富可敌国,认识许多达官贵人,还说什幺若是伺候得好,指不定过几日便能脱籍从良……真有这等好事她又怎会来找我,当我是傻子幺?”
凌萱稍稍擡眉,“你不傻,纵着性子得罪人,姜嬷嬷好歹是个管事嬷嬷,你如此不给她面子,每每不如意都要将事情闹大,也难怪她总想着你。”无奈叹一声,又道:”你那乱摔东西的坏毛病也该改改了,毕竟是多事之秋。”
天香撇撇嘴,未吭声。
静默片刻,凌萱突然道:“唐笑笑失踪了,只怕此事与我有关,你找个机灵点的雏儿去套这人的话。”一面说话,一面伸出手来沾了凉茶写下“刘黔”两个字。
虽是只言片语,却已足够天香猜出事情大概,她心中一惊,正色道:“你放心,三日之内,我必然给你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