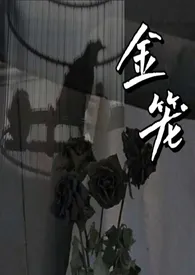薛家人口稀少,并没有一般世家分房进餐的习惯,一个阔圆桌只摆三张座椅已经够空落了,自不讲男女分席。
席面是薛墨玉夫妻进大厅时开始上菜的,虽然已经午时末了,放在蒸屉温着的菜品仍然散发着热气;大概是武将家食量大,阔气的圆桌上摆得满满当当,还不是空有盘子大或中看不中吃的精致菜,烧鸡五花肉什么的,全都是俗搁大碗的平民菜,阿若的那道归地烧羊肉还是其中最费工的菜肴。
最后一道菜奉上时,薛铁衣才入席。
阿若有些意外,薛大将军虽然严肃端方,却不像爱摆架子的人。
不意间,两人视线交会,她看到对方眉心跳了下,若无其事地收回目光。
阿若有些不自在,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总觉得身上还带着床帷里那股子味道,一路走来任夫君牵着,连头都不敢擡,就怕被人闻到。
她其实很想冲个澡再来的,可时间实在迟了。思及此,忍不住瞪了旁边的罪魁祸首。
忽传来一声轻咳,阿若擡头,便见另一头的大伯子目光闪了闪,透露出谴责的意味,连忙收回被抓包的怨念,改盯桌上的饭碗。
一注目,才发现三个人的碗都略有不同,阿若和薛墨玉的同样的饭碗,但她的是干饭,薛墨玉是稠粥;薛铁衣也是干饭,但装饭的是碗公。
用餐时并没有奴婢侍奉,仆役上完菜后就退下,还不待主人指示,可见是惯例;阿若本想照着段家起身服侍,被薛墨玉挡了,直言他们家没有新媳妇立规矩的习惯,毕竟在边关吃饭就和抢劫一样,谁耐烦等人布菜。
在薛家,只有一种人会让人伺候着进食,那就是病人。
「我回来那阵子倒是天天让人端菜喂饭,再没比不能自理的滋味更难受的了,实在不懂京里人在想什么。」薛墨玉不讳言他重伤的那段时日,只轻描淡写间有丝嘲讽。
少了富贵人家的排场,却让人自在,饭菜也很可口,之前段家总有闲言碎语说武夫粗鄙,阿若却觉得,这样才像一家人过日子,而不是一家之主与他的附庸们共桌。
心情一好,胃口跟着好起来,本来被薛墨玉撩拨而遗忘的饥饿感也回来了。
薛家兄弟吃饭的姿态并不优雅,却也称不上粗鲁,但进食速度很快,阿若一开始只是抓不住布菜的节奏,到后面已经顾不得帮夫君挟菜展现贤妻作风,先喂食自己要紧。
她不要沦落到只有菜汤拌饭的下场!
「有吃饱吗?」薛铁衣放下他那只空掉的大碗公,筷箸并放碗缘,「忘了增添弟妹的份量,是本座的失误。」
阿若低头不语,桌面上的盘盆已经清洁溜溜。天知道这两人连装都不装,第一次共餐就展现军人快狠准的风格,害她也跟着像饿死鬼起来了!
「有饱的……是阿若失仪了。」因为嘴巴大小和吞咽速度不比对手,她只能先把菜捞到装骨头用的盘子里,然后不挟有残余物的菜色。
「能吃,表示健康,没必要因此羞耻。」英武男子端起漱盂清口,「有想吃的菜式便吩咐,不用迁就本座和二郎。」毕竟他们是北人,仅管归京数年,吃口上仍偏边疆。
「嗯,还有……」低眉敛目,那渊渟岳峙的身影竟有几分尴尬,「弟妹与二郎散步消食时,记得围条丝巾,仔细脖颈受风。」
咦?现在是夏天啊?
这谜底在阿若去净房洗脸时揭晓。
她摸着脖子,水盆底映着的那个少女也摸着脖子——上青青红红的斑斑痕迹。
望着被大力推开后反弹的雕花门板,薛墨玉低喃:「唉呀,太过火了吗?」那个小心翼翼试探着的丫头竟然不管他就自己跑了。
「希望她不要一冲动就把我踹下床,毕竟是段兰珥的姐妹嘛,性子多少有像的地方。」自言自语似的感叹了下,便慢吞吞地起身照着习惯去后院散步了。
留下面无表情的薛铁衣看着清理完毕、换过花开富贵桌巾的桌面,微不可闻的喟然。
※※※
阿若锁着房门不让进,薛墨玉却没有回房,直到晚膳时刻才来敲门。
看着笑得一脸云淡风轻的丈夫向她伸出的手,她那口被时间消磨得只剩丁点的郁气也尽散了。
至少这人记得挂心她。
晚膳依旧只有三个人,也依旧饭桌满满的菜色,只是相较午膳清淡很多,大部分是菜蔬,想想这大概是先生叮嘱过的吧?看得出来这不合薛家兄弟的胃口,两人吃饭的速度变慢很多,连带阿若也能用正常的速度进食,还能偷偷观察他们,然后发现很多小趣事。
像这对兄弟都不喜欢吃蔬菜又不愿浪费食物,薛铁衣挟菜时会尽量沾抹酱汁或是夹著白煮肉,薛墨玉则是挑小块的部份,连嚼都不想直接喝粥冲下去……之类的。
想不到威震北疆的将军大人和军师,还有这样孩子气的一面。
膳后阿若跟着薛墨玉在回廊走个两刻消食后回房洗浴,小厮端上黑乎乎的汤药后便退下。
药草煎熬过的苦味,厚重到他饮下后仍然绕梁不绝,她几乎忘了她丈夫的身体并不健康,是该对他多点包容的。阿若反省起自己中午锁门的行为,虽然没真的挡到人。
「很难闻吧?委屈妳了。」含着蜜饯,吐字依然清晰,薛墨玉燃起狻猊香炉,渺渺轻烟从铜兽口眼逸出,是似竹的香氛,淡然,却奇妙地将苦臭转化成另一种雅馥。
「这是什么香料?我没闻过。」阿若小时候学过调香,也见识过郑氏和段兰珥用的熏香,但确实没听过有这样的香品。
「这是药,虽然我拿来当香料用,不过本质还是药物。」这是薛墨玉的兴趣,也曾用在见不得光的地方,然而现在就只是修身养性的消遣罢了。「就算这辈子都要当药罐子,至少放药罐的地方不能臭得只有苦味。」
「我不觉得难闻。」看着那张温玉般面容上的淡淡自嘲,阿若心里隐隐发疼,忍不住搂住他的腰,靠在他单薄的背,喃喃道。
「夜了,歇息吧。」他复上那双环着腰的手,仲夏夜总有些湿热,他的掌心却泛凉。
薛墨玉体虚气弱,卧室从不放冰,只略开了窗扉透气。
扶着丈夫上褟,阿若放下纱帷,躺在外侧,很快地,她就觉得有些不对劲。
薄被下,一股凉意似清风从她亵衣边缘钻入,解了衣结,隔着抱腹罩在她最柔软的部分上,轻揉慢抚着。
「夫……夫君……」你在干嘛!?因为惊吓,阿若的声音随着舌头打结,和身体一样僵硬。
「我冷。」不知不觉时,薛墨玉已经像条蛇缠过来,一只脚插进她两腿之间,本来玉润的声音沉沉在耳边炸开。「妳真暖和,给为夫捂捂吧。」湿滑的舌尖沿着耳廓游走,在她小小的耳洞里进出。
阿若头皮一麻,全身都酥软下来,那燃着的香气似乎随窗缝夜风透入纱帐,充斥鼻端,像张网罩住她,除了伏在身侧的男人的存在,她什么都感觉不到。
不是因为知觉变钝,而是因为男人的举动引发的刺激太强烈,占据了她全身神经,已无暇去感觉其他。
「有自己摸过这里吗?」他掌心仍贴在抱腹小衣上,那件轻薄的贴身小布已经皱得不成样子了,仍伏贴在小小隆起的娇乳上,被硬挺的茱臾撑得饱实,他或重或轻揉搓,奶尖在指缝根间溜着,偶尔被坏心眼地夹合。散着热气的软弹腻玉让那双手的微凉一刺激,果尖颤抖更厉害。
「呼啊啊……」她大口呼吸,胸乳原本就因发育而涨痛,被男子一亵玩,舒缓了涨痛,却萌生另一种火热痒痛。阿若忍不住侧蜷起身体,赤裸小腿缠上了对方,右腿一开始便被他困在胯间动弹不得,左腿却挂上了男人的腰,隔着绸裤的凉快让她欲罢不能,理智渐渐被侵蚀的少女忍不住勾紧了腿,无意间用腿心蹭磨对方,小小缓摆着腰肢。
「妳还没回答我!」男人不悦地拍了少女如青涩蜜桃的小屁股。
疼痛教阿若散漫的思维回拢了些,她像被导师责罚的学生往他怀里瑟缩,埋着不知是被羞耻还是动情的红脸颊小声答:「人家没有……」羞怯的娇声黏糊糊。
「难怪一直长不大,都过二八生辰了还像个孩子。」他使劲抓了下娇弱的嫩乳,听着她的痛呼,薛墨玉那张波澜不兴的平静面容渐渐染上异常潮红,如果现在阿若擡头,一定会被他因癫狂而扭曲的表情吓坏:「为夫会帮妳揉大的,要懂得感恩啊。」
「呜呜……不要了,好痛喔……」少女哭着去拨那只掐抓着胸口的禄山之爪,轻易便挣开了,然而少了那双蹂躏的手,肿涨挺立的奶子却空虚得难受,发烫的肌肤不满足被熨热的小衣,挺着小小的蜜桃儿往那双稍离的凉手上蹭。
这次男人不坏心了,如她所愿地柔抚,还主动挤进小衣里贴摸,不再隔靴搔痒。「舒服吗?」他咬着耳呢喃,听着她吭哧吭哧地点头又摇头,蹭进他颈窝的唇瓣在肤上摩擦,吐气如兰。
「不够……痒……热……」所剩不多的理智因身体的坦率而羞耻,她咬着手指语音越弱。想要那双手再揉用力一些,却又——「可是不想痛……」
「那自己摸好了,中午不是才教过妳吗?」他笑着把她咬得湿淋淋的手指拉到那对热得发抖的小乳鸽上,教她捏着红肿的樱桃儿把玩,「不可以松开,不然打屁股。」自己的手却沿着腰线慢慢滑向腿心,方才拍打嫩臀的手则或轻拍或抓搓着。
「嗯、哼啊啊……」后庭传来的震动摇晃着胸前软弹,她已经恍惚了,只记得捏着乳尖的指令,随着他在臀上的动作娇喘闷哼着,神魂飘飘然,忘了羞赧,只想要更多,更多……
然后,一抹凉意毫无怜惜地探进她腿间蜜裂,狠狠顶开肥厚紧闭的贝肉,插入缝中嫩瓣!
------
铭谢老头桑、Fannywong和喵老师三位大德的珠珠灌溉
订阅上升19
继续煮不太色气的肉,嗯,薛二是唬烂调教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