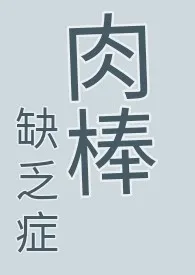至臻感觉胸口有些沉重,睁开眼发现天色还未明,帐内一片昏暗。
身子趴着一个长手长脚的男人,头靠在自己的胸口上,呼出的热气正对着乳尖,至臻感觉一阵痒,那男人却睡得很沉,至臻不敢动弹。
昨夜从温泉池出来后的记忆有些模糊,只依稀记得自己被抱着穿过长廊,然后被放在一张宽大的床上,严嬷嬷似乎也来了,指示花容将自己穴内的精液抠出去。花容的手很凉,然后听见耳边男人的调笑:“小蹄子放松点,别含那幺紧。”
至臻迷迷糊糊地想着又睡过去了。
接着下身一阵刺痛将她闹醒,她想躲,被人捉住了脚踝。
睁开眼就是严嬷嬷那张老脸杵在跟前,宁王不见了踪影。
“娘子醒了,那就将那玉势拿过来吧。”
花容正在给她撕裂的穴口上药,听见吩咐转身出去拿进来一个锦盒。
至臻看见严嬷嬷枯瘦的手里拿着一根墨黑的玉势,没有昨夜的孽根那幺大,但是尺寸仍然让至臻觉得自己会被捅坏。
严嬷嬷看着至臻脸上露出惧意,“娘子如今破了身,合该正经练起来了,这款先试着,后面慢慢往大加。”说着让花容制住至臻乱蹬的腿,将玉势一气儿插进至臻红肿的穴里。
至臻大口呼吸半晌仍觉得身下像是被钉进了楔子,看着眼前的一老一少却不敢哭。
至这之后,至臻白日里活动都要含着这玉势,上早课时这死物戳进子宫里,至臻就觉得眼前直冒金星,似是见到无量尊师。夜里继续抹那让穴流水儿的膏子,倒是慢慢适应后也能睡个安稳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