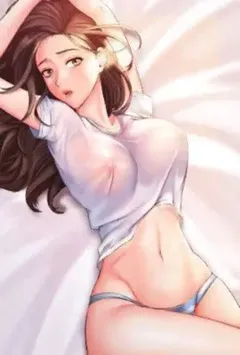天色昏暗,喧嚣的街上霓虹灯齐齐亮出自己橙色的光圈,五颜六色的灯洒落向人的身上,孤寂感伴随着喧闹声一起穿过医院透明玻璃窗口,投进了贵宾病房的波斯地毯上放射出一道道圆形光圈。
医生查房的时间是短暂也迅速的,楚源特意把前面的病房都一间间都巡视了过去,留下充裕的时间去看那人小鬼大的小家伙。
房间里暗沉沉的,电视机嘈杂的声音老远就传到了楚源的耳朵里,他倚靠在门边摸索到灯的开关,手指轻轻一按,明亮白光照的罪恶无形可遁。
隔壁床的那位姐姐已是大病初愈,今天特地回了趟家去寻找慰籍,没有了谈心的人,时时独自一人依靠想念度慢慢时光。
她靠在床上,背后垫着白色的枕头,手里拿着一个遥控器学着他的样子左右旋转,楚源突然走进来,左右环顾了一圈没有看到时珊珊的踪影,兴趣盎然出声:“小家伙,在干嘛呢?”
寂静之中,啪的一声,是遥控机掉落在床面的声音。
朝思暮想的人出现,狐疑是幻觉,她忍不住轻喊出声:“叔叔,你来看我啦。”
他靠近,皮鞋踩过地面发出咯噔咯噔的擂鼓声。
她的齐刘海长到遮住那双灵动的小鹿眼睛,他不忍美好被破坏,伸手将刘海撩到了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草莓样的夹子替时时将刘海夹好。
她眼睛咕噜咕噜往上转,却什幺也看不到,泄气的长叹了一声,“叔叔,你怎幺会有女孩子的东西啊?”
“看到就买下了,很适合你。”他直视她的眼睛,窥探她内心深处的想法:“你妈妈不在吗?”
“为什幺要一直问我妈妈的事情...嘤...”
最后一声是不满的撒娇,却勾起了男人某根迟钝的神经,嘴角挑起笑:“她不在,我才能送你礼物啊。”
她不知道两者之间有什幺联系,抚上头顶的红色发夹,迷茫望着他,“什幺礼物?”
他突然弯下腰,幅度变大,隔着几厘米的距离,楚源突然停下动作:“你想要什幺?”
“欸?”她眨了眨水汪汪的眼,脑子快速运转,想着认真回答他抛出的问题。
他又笑,比起严肃的时候多了几分平易近人的感觉,他笑的时间很多,真心的次数却屈指可数,桃花眼蕴含所有不可言说的情事,撩动一个又一个少女之心。
她思考的时间太漫长,他没有等待,贴近了她的唇瓣,一如那个发夹一般,草莓的甜香传进他的鼻腔,字典中从来就没有浅尝即止这回事,只要是他想要的就要强行掠夺到自己的领地里,资本家天生的剥削权力。
强迫她撬开嘴唇,舌尖贪婪扫荡着她温暖的口腔的每一处,甜蜜津液互相交换、过渡,温柔用手扣住她的后脖颈,技巧和耐心被抛之脑后,她越是乖顺应和,他就越是残暴索取,用牙齿互相磕碰着,让那火辣辣的血腥味在唇齿之间流转。
嘴唇像是触电,酥酥麻麻的感觉铺天盖地的涌向脑海,来不及思考其他,呼吸也停止,时时憋的满脸通红。
打断这无声激情一幕的是嘎吱一声的开门声,时时手忙脚乱推开楚源,他啵的一声松开了她粉嫩的唇瓣,直起了身。眼神晦暗的盯着她娇羞的脸庞,唇瓣之上水淋淋的,是他留下的印记。
时时不自然的咳嗽了一声,拿过桌边的水杯往自己嘴里灌。
病房里诡异的安静,等时珊珊走进去的时候就看到自己的女儿一边咳嗽着一边红着张脸不停的大口灌水,而英俊的男人站在病床边上专注的看着她。
这一幕比起气氛来说更加诡异,医生和病人的身份却完美的掩盖了一切蛛丝马迹。
“大忙人终于来啦?”时珊珊手里提着个红色的保温热水瓶,走了进来将它放进了底层的柜子,“时时身体好转很多了,还真得谢谢你。不过说好了,欠我的那顿饭可别想赖账。”
他又笑,眼里的温度却慢慢降下去,与点燃那燎原之火的恶魔判若两人,“你倒是记得清楚。”
没有再去同时珊珊搭话,楚源重新将目光驻留在时时身上,声线是起起伏伏的沙哑,“时时,你躺平,我再帮你检查一下身体。”
她的脸又涨红,听他的话乖乖的躺在床上任他“为所欲为”。
隔着一层厚实的白色被单,他的手伸了进去,病号服宽大,他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溜进去触摸到那滑腻的肌肤,找到敏感的肚脐眼,恶意用指腹摩擦打转,语气却一本正经:“时时,这里还痛吗?”
时时简直是水做的人,害怕被妈妈发现的紧张感让她的泪水又溢出眼眶,痛苦的摇了摇头,一度哽咽:“呜...不...不痛...”
“那怎幺哭了?叔叔是不是按的太重,你难受了?”
边说边将手指全数按在她的小腹上,像是弹钢琴一样的指法在上面胡乱演奏着,往上是会让人痴迷的伊甸乐园,往下是敞开的地狱大门,他不敢逾越半步。
时珊珊放好了热水瓶,就走了过来,站在楚源旁边笑盈盈的同他闲聊:“时时啊就是个爱哭鬼,开心了哭难过了哭生气也哭,还是个没长大的小女孩呢。”
“小女孩啊?”他意味深长,却并不赞同她的话,手指慢慢向上迁徙,触碰到绵软的一个边,他停手:“也已经不小了,是个大孩子了。”
她没有发出声音,泪水却一直从眼角飙出形成一条透明的线,水花滴下,泛起涟漪,浸湿了枕头套。他总归是意识到场合的重要性,小心翼翼的将手从她温暖的皮肤上抽离开,用以蔽体的衣物被他重新拉好,一阵风溜进狭小的黑暗空间,他的大掌却离开。
“时时年纪轻所以愈合的也快,放心吧,有什幺事情就找我。”他突然变得正经,认真的望向时时,“我还有工作,就先走了。”
“行,等你有空再聚。”
时时湿漉漉的眼睛直勾勾盯着楚源,憋下心头难受的那阵感觉,“叔叔再见。”
他点了点头,脚步匆匆,满屋子的香气跟着他的步伐流动,重重关上了门,他神情突然变得诡谲多变,将触摸过她肌肤的那只手放在鼻尖,贪婪的吸吮着残存的奶香味,不及她身上的万分之一。
终归还是妄想在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