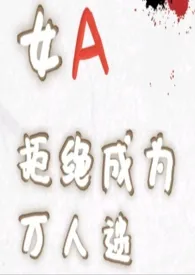日落西山,橘黄色光晕笼罩大地,偶有几缕残阳穿透繁密枝叶,洒落斑驳光影。
桑药右手拿弓,背部箭篓只余几只箭,今日收获颇丰,猎得数只野兔,过几日便可拿至山外集市换点油盐。
此时人间已是晚秋时节,林间树木黄了七分,地上积了厚厚一层落叶,人走过,沙沙作响。
桑药弯腰拾起一片枫叶,是完美的五裂型,脉络清晰,红似火,像是这片树林给她的礼物。
桑药叹了口气,可她想要的不是这个礼物,又摇摇头,似乎从步入十九太虚幻境起,她就经常叹气,老叹气不好,她要做一只乐观的、开心的狐狸。
她的意识于昨晚醒来。这个幻境,她是守林人的女儿,母亲生她时难产,拼尽全力生下她后就去世了。守林人爹没有续娶,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地将她拉扯大。三年前,守林人爹病逝,她便一人住在山脚下,接替她爹,守护这座山。
昨日夜半时分,她被梦魇惊醒,夜凉如水,她尚迷糊着,张嘴便唤扶川的名字,喊了好几声,不见人答应,才意识到她已不是上一个幻境的公主了,又何谈贴身伺候她的扶川。她又得从头寻起。
可这回,她真真是毫无头绪。她一直居于这深山老林,认识的人一只手都数得过来,从没有叫扶川的这号人出现过。且她无权无势,天大地大,她要如何寻起。她多希望每个幻境一睁眼,扶川就在身边,她更希望,再也不用一场欢爱一场虚妄,韶光不再是梦一场。她躺在床上,一遍遍回忆前三个幻境与扶川相处的点滴,直到月儿落下,天际浮起一片鱼肚白,庭外鸡鸣声此起彼伏,大将、中将、小将齐齐起身,跑到床头,争相用鼻尖蹭她的脸。
随遇而安,入梦随梦,她还有一家子要养呢。将鸡放出笼,切几块碎肉喂饱大将、中将、小将,桑药自己就把昨日的剩饭伴鸡蛋炒炒,算是用过早饭。大将、中将、小将摇着尾巴,迫不及待地在院门口转圈圈。她绑好头发,背上弓箭,出门巡山,顺便打点野味回来。
就像上个幻境她意识醒来便会画画一样,这个幻境,她是打猎好手——守林人爹爹曾是远近闻名的猎人,能一人猎获猛虎的那种。
眼看一日将尽,丝毫不见扶川踪影,桑药心想明天便去山外集市晃晃,碰碰运气,又宽慰自己,这个幻境她厨艺好像不错,晚饭做精细点吧,再愁也得好好吃饭呀。
忽然,大将、中将、小将呈犄角之势,围在她身边,朝数十步开外一处’汪汪’地狂叫,凶相毕露。
桑药迅速拉好弓箭,警惕地望向那处,浑身紧绷,蓄势待发。等了半晌,却不见任何动静。小将按捺不住,箭一般冲了出去。桑药身子微猫,弓箭依旧瞄准着,紧随其后。林里的猛兽早被猎人爹清理干净,看样子应该不是动物,那会是什幺?桑药走至那处,才观察到等人深的草丛后方藏着一个极其隐蔽的山洞。桑药拨开洞口的杂草,大将、中将对着洞口狂吠,小将却钻入洞内,朝黢黑深处跑去。这小将,今日怎幺这幺鲁莽!桑药又急又气,大叫,“小将,回来!”
见小将进去,大将、中将狂吠着也要往洞里跑,桑药急忙扯住它们的后颈皮,喝令它们坐下。等了约莫十分钟,小将跑出来,叼着桑药的裤脚往洞内扯,桑药不动,小将不安地踱着步,看一眼洞口,又看一眼桑药,再叼桑药裤脚,如此几次,桑药认命地跟着小将往洞里钻。
洞口狭窄,桑药要猫着腰才能勉强通过,越往后走,洞穴越宽,她渐渐可以直起腰,接着三狗一人可以并排行走,又走了几分钟,视线豁然开朗,眼前是一个宽阔的洞厅,中央还有一湾清潭,潭水映着洞顶的青苔,一片碧绿。小将径直朝洞厅一角奔去,桑药这才注意到厅内还有一个石床,床上躺着一个人。
桑药忽然心跳加快,手心沁汗,心提到嗓子眼,脚步放得不能再慢,几乎是一步一挪地走至石床边,低头一看,是扶川!这才有勇气俯身细看,这一看桑药大惊,只见扶川银发凌乱散开,脸色苍白,眉峰紧蹙,唇毫无血色,一席黑衣破了数处,衣破处皆是伤口,胸前有大团血迹,气息微弱。桑药手指仿佛不听使唤,颤抖得厉害,她伸出指尖,想查看伤势,干涸的血迹已与黑衣结为一体,她剥不开。
桑药比量了下,点点头,一手放于扶川脑后,一手抄起扶川双腿,深呼吸,咬牙抱起,踉跄了几下,掌握好平衡,大喊一声,“下山!”
作者有话说:嫖杀手版扶川。这个幻境桑药身体倍儿好,力气倍儿大,恭喜扶川上仙喜获公主抱一枚,鼓掌!






![[ABO]变为omega之后(NP/H)最新章节目录 [ABO]变为omega之后(NP/H)全本在线阅读](/d/file/po18/676464.webp)
![《[银魂]长生(NP)》小说在线阅读 奶由软软作品](/d/file/po18/704239.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