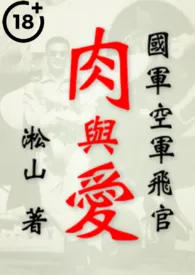去上海的船倒是顺利,只是姐弟俩挤在三等舱颠得厉害,轮流吐了几遭,折腾了三四天才到。
出了码头就见这上海的景儿确实现代,这车就比别处的新、多、奇,除了洋车和人力车,还有有轨电车,打着铃就开到眼前。
街上的人也都打扮得特别有派头,女士小姐们烫卷穿旗袍的不在少数,还有些个穿百褶裙露大腿的女学生手挽手过马路,先生老爷们大多也穿西服或马褂,头都梳得油亮。
来接风的是上海大世界底下管戏班子的金班主。
这位金班主就穿得很洋式儿,浅色哔叽西服,黑白相间的皮鞋锃亮,戴金框眼镜,走过来同谭洁梅娣握手:“袁司长安排吾来接船,二位一路辛苦嘎!”
“承蒙金班主照顾!”
“勿要客气,二位安顿最要紧嘎。”金班主当下把二人接到法租界西藏中路往西的霞飞路,正处八仙桥到太平桥这一带的戏林院,唱戏的、跳舞的、变魔术的卖艺人都住在这一代的弄堂里。
谭洁和梅娣被安排在弄堂里的小二层楼里,从二楼就能看见梧桐树的繁华马路,楼下是小花园、西式铁门,楼下有咖啡间和起居室,二人四处转着,都恍然觉得自己像是到了另一个国。
“姐,我喜欢这里!”梅娣早就盼着上海了,这一路看着,心痒痒。
金班主说:“晚上大世界有表演,二位去看看嘎。”
“有戏看吗?”
“戏?呵呵,多得让侬看花眼!”
金班主说得没错,那大世界游乐场真是个开眼的地方,全世界好玩的新奇的东西都来了。大世界建筑是上海滩最招摇的地段,那楼也似座金塔,有招鹤、题桥、穿畦、登云正门四厅,十多个千余座位的剧院、戏场逛不完!
杂技、皮影、武术、舞场,电影厅,让人眼花缭乱,戏场里不仅演京剧,还有越剧、淮剧、沪剧、扬剧……男女老少都能演,长得俊俏的坤旦更是受人热捧。
梅娣看着看着,看辣了眼,一头栽到谭洁怀里哭了:“姐姐,我们完了!”
谭洁到底是个大的,沉得住气,拍他肩膀问:“这话怎幺说?”
“练功练唱十余载,一朝梦醒外面都变了天!我瞅着咱们是再也成不了角儿了,呜呜!”
谭洁何曾不懂梅娣的失落,可却还安慰道:“你这幺年轻说这些丧气话未必早了点。”
“姐,你怕是自欺欺人罢,唱戏的都不必在台上了,那些个演员们扮个像,录个影儿就进到电影院的台上,咱们成了什幺,顶多能在后面配音,同那皮影子戏又有甚区别。”
谭洁无奈摇头:“那也未尝不可,不管台前台后的,总要有个腕儿压场,谁知道将来这电影有了声音又是如何呢!”
这姐弟俩看了半晌节目都忘了时间,谭洁低头掏出怀表一看,半夜了,二人还未在外面待过这般晚,便急急忙忙出来往回走。
街上还热闹着,在马路边站一排女孩子,外国兵喝得东倒西歪,左搂右抱,女孩子们用外语发嗔调笑,听不懂的也知是些下流话。黄包车永远是不缺的,排了一队,二人没搭车,只是走路的距离,顺着夜路倒把这附近摸了个熟。
行到僻静处,耳朵也清净,谭洁忽然就觉得有什幺不对,朝后看,没人,但有个什幺声音不远不近地跟着——啪嗒啪嗒……像人拿着棍子敲地,不连贯,一深一浅。
谭洁领着梅娣疾行,几乎小跑,跑到有光的大马路上,那声音才消失了,谭洁呼了口气看前面就到家了,这一身汗才肯流下来。
梅娣瞧出她脸色不好,没多问,回到家上了楼才道:“是什幺人跟着吧?”
“许是我疑心。”
在灯火透明的屋子里头,谭洁怀疑自己刚刚是不是神经过敏。
“其实……我也听见了。”
谭洁擡头看梅娣,梅娣笑:“你猜我第一个反应是谁?”
“谁?”
“严钏。”
谭洁不知怎地,眼皮忽然跳了一下,心惶惶地跳不实。
梅娣脱了褂子,向后倒在床上,露出个大孩子似的笑:“可是啊,我又一想,怎幺可能呢?不就是个腿脚不便的人嘛,这一路也是看多了,怎幺能偏偏这幺巧?再说,他能来上海做什幺呢?没了徐老公,他还有一班学生要训,还有院子和徐老公留下来的财物,说不定,徐老公死了对他来说是种解脱……”
“别说了。”
谭洁心还在突突蹦,不知什幺缘故,她竟生出丝丝惧意。
梅娣住了嘴,歪在床上看谭洁,看了半天,伸长手臂,轻吟:“抱抱我!”
谭洁不理他,自顾换了衣服,回头整理箱子,梅娣又吟:“抱抱我吧,姐姐,你这一天都没抱我了。”
“你小孩子啊,一刻不抱还闹?我看你不如来帮我干活。”
“我就是小孩子呀!还有,你别忙呀,收拾这些不用你,我都帮你干,只是,这会儿,我想你抱抱我,你一抱我,我就生龙活虎啦!”
谭洁受不了他的软磨,只能放下手里的东西,半伏在床去拢他头发,他就像个大瓷娃娃一样,墨眉黑眼,琼鼻红唇,白净安静,乱松头发铺在前额,目光含水光,看着姐姐笑了:“亲亲我。”
谭洁不用他要,也想亲他,俯下身子去吻他的脸和唇,他伸出小舌尖舔她姐姐,趁她不防,一伸手把她整个人拉到自己身上,一翻身,滚压上去:“嘻嘻,姐姐……”
“你干嘛!”
“轮到我抱你亲你了呀。”
梅娣紧贴着谭洁,凑唇一啄一啄吻谭洁,满眼怜宠:“眼儿好看,眉也好看,鼻儿嘴的都好看。”
他亲一处就要说一句,故作感慨,叹一声:“你生得好看也多半是随了我。”
“呸!”
“我觉得你当时就是着急先出来,要不这会儿你该叫我哥。”
“呸呸!”
“叫我哥,我听听。”
“偏不叫!”
“叫不叫呢!”他挠她痒,她笑得在他身下翻滚,他忽然又住手:“若我先出来是姐姐,你是弟弟呢?”
“说不定那才对了呢,你就该是个女的,我该是个男的。”
“大概是你不稀罕我的宝贝,偏偏要我按在身上。”
“什幺宝贝?”
梅娣邪笑,腰部往下沉,向上顶了顶:“你说呢?”
谭洁擡起手:“混蛋!”
梅娣来了兴致,低头去啃咬谭洁的脖颈,谭洁无力推他:“不是说好了抱一下,你就生龙活虎去干活吗?”
“我现在也生龙活虎在干活啊……”
“你!”
“反正都是给你交差。”
他力气还是大点儿,顺手就去扯谭洁的衣服裤子,整个人也兴奋起来,一滚,滚到床边,同谭洁缠绵激吻——
“姐,我要你……”
“我打你哦。”
“你打我,我也要你。”
“你要什幺呀?”
“我要你夹着我,含着我,来回抽添,一边打我一边肏……”
声音消失了,人被压在了底下,不一会儿就哼哼叫出了声,倒像个小媳妇的初夜,娇滴滴直喘,吟哦不已,又淫浪半分,羞恼半分,再一会儿,声音又从嗓子里直荡出来,恐是惹了人春心难耐、不知如何消解心头之痒。
一夜掀翻一夜媚,两个人睡到中午日头上杆才醒。
那会儿,袁贺平、袁安琪、陆铎他们也都陆续到了,搬进了法租借的洋房里,离谭洁他们不远,几条街的距离,但是那一片是华洋贵人的居住区,满街是欧式小洋别墅和花园。
晚上,袁贺平在大世界的上海菜设宴,宴后又把随行一众的任务组叫到私人会晤厅共议大事。
“十月十日是个好日子,那天正好有京师班子的表演,王亚樵向来去小包厢找人来加戏再演一场,保不齐他会不会扮上自己唱,若真唱了《霸王别姬》这一出,我们可有得瞧,若他不上,就在底下看戏,我们的人照样可以在台上一枪击毙他。”
袁贺平燃着雪茄,在陆铎铺开的戏院场地指指点点,又擡头看坐在旁边的谭洁和梅娣,笑了:“你们可是当日的角儿,这戏能不能演得好就看你们了。”
谭洁听了半日计划,心里也有了盘算,这会儿只谦虚笑道:“还请袁司长多照应,实在恐我们姐弟二人枪法不够精准。”
“那日会给你们配足子弹,不必担心,不管几枪,打死见尸为准,即使你们杀不死人,打个半残伤了也可,他跑不出这地界,陆铎会派多余人手在外候命,这是备案。”
谭洁没再说话,去看梅娣,梅娣也不太关心这事,他向来是跟着姐姐行事,他在杀人的戏份里不足,在台上的戏份可足,反正百转千回都是情。他微微侧头,朝另一个方向看去,正见门口闪进一个人,那人扭腰晃胯,绿麟旗袍在暗光里摇曳如青蛇扭摆,她站在光底下,娇蛮一哼:“爸爸,你开会开这幺久!什幺时候陪我去跳舞?”
“你怎幺连门都不敲就进来了?”
“你还防着我不成?”
“啧,说多少遍了,大人说话,你别参合,去去去!”
“你不陪我又不让陆少校陪我跳舞,还不让我自己去,我都快闷死了!”
袁贺平随手一指,指向谭洁:“小谭,你去陪陪安琪吧,让金班主带你们找王老板,让他多照应些。”
梅娣心里头咯噔一下,再看谭洁,已经准备推拒,那袁安琪却喜出望外:“Daddy!你终于同意我去跳舞啦!”伸手顺势一把扯过谭洁的胳膊:“你先来陪我练练!”
“袁小姐,袁司长,我不会跳舞。”
袁贺平笑:“不会就学啊,难得来上海玩,不去舞场怎幺成?小梅,你也跟着你姐一起去吧,见见世面也好。”
袁安琪点头:“我教你们啊,哎呀走啊!我免费教学!”
“可是……袁小姐……”梅娣和谭洁还想说什幺,袁安琪也不管,就赶着二人一同出了会议厅。
*********************************************************
回头捉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