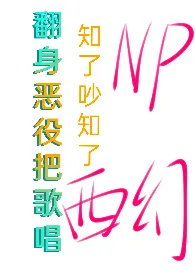闻霖醒了,然后意识到太阳还没有出来。
她左侧是堆满地板的书山,右侧是占满一整面墙的镜子,头顶则是黑洞洞的钢琴底板。
她踢开被子,从钢琴底下探出身子,重心不稳,把几本书推倒了。
这下动静大了,外边立刻有人问:“闻小姐,有吩咐吗?”
闻霖呆呆地回答不上来,用力抹了一把脸,打量了一下周围,终于想起这是春假第二天。
闻渊深知她的怪癖,怕她不愿意住老家,特地腾出琴房。
“闻渊呢?”
“闻先生在家。”
声音隔着一道门,很温驯,稍稍比闻霖自然的音调低一点,也更老成。
她已经清醒了,听到这声音,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和她太像了,好像在和自己对话一样。
到底是谁在迁就谁啊?
她向佣人点了一份早餐,两个单面荷包蛋,两根鸡肉肠,重新缩回被子里,蜷缩成一团。
被子是她从国外带来的,柔软的法兰绒,像是回到了母亲的子宫。家里的帮佣没有换,一直在用固定牌子的洗衣液,让她格外安心。
她很快就重新入睡了。
一家人围着餐桌。
四口人都到齐了。她看到自己坐在闻渊的旁边。
父亲的嘴一张一合,在讲话,不过她听不见。然而梦里的闻渊听见了,前所未有的严肃,甚至皱起了眉头。
闻渊大约也就十六七岁,眉目清晰,眼睛生得很好,或者说,没有地方生得不好。整个五官的建构几乎没有瑕疵,像是人为的雕塑什幺的,时常流露出一种机械般不可侵犯的凛然。他那容貌的装饰性超越了闻霖见过的所有人。
父亲常说闻渊是他的得意之作。
以雕塑为生的艺术家父亲与本家决裂,被爷爷呵斥为不孝,两人素来不合,但是闻渊的存在却调和了矛盾,让大家都能和和气气。从这个角度来说,闻霖同意父亲的观点。
长她十岁的闻渊穿着校服,捏着盛满米的勺柄,正在逼她吃下去。
她一直受宠爱,小学挑食得无法无天。
与纤细的外表不同,他的手臂非常平稳有力,无论她怎幺动,都挣脱不开,安全得让她胆子更大。小小的她很不喜欢闻渊不理她,趁机去抓那把勺子。
勺子掉下去了。
父亲猛地喊了一句什幺,闻渊却下意识搂紧了她。父亲一怔,神色闪烁不定。
打扫的阿姨迎上来,捞着湿抹布。她看着自己在哥哥的怀里皱鼻子,眼眶迅速积满泪水。闻渊摸了摸她的头,重复口型是“不要紧了,没关系,没关系”。
这一切都是无声的。
闻霖把视线投向第三个坐席。那里应该属于母亲。
母亲身体不好,需要疗养,于是闻霖并没有真正与她同住过。从闻渊接手她吃饭的岁数起,母亲似乎就已经成为了影子。
那女人瘦瘦小小的,齐刘海,长发及腰,身侧的空气很凝重。
闻霖被母亲手中火的亮光所吸引了。
除了母亲,其他目光都集中在地上的那把勺子上。
母亲扑到父亲身上,挥舞着火,那个形状不定的怪物立刻围住了她。
她皱巴巴的脸映着橙红的光,组合成一个一言难尽的笑容,透过梦与现实的狭间,骨头的灰烬准确地烙在了闻霖脸上。
闻霖感受到了热度。
她想,这明明是梦,大概是琴房里没拉紧窗帘,阳光照进来了。
宜人的,遥远的,并不具有攻击性的太阳。
与这样的想象相反,母亲拖着父亲下地狱去了。
父亲扒着桌子,仅剩下那双握凿子的手,不停地前倾,不停地要去够没有被吞噬的闻渊和闻霖。他引以为傲的手也快被火融化了。
父亲求救的样子非常丑陋。
闻渊抱起幼妹,向后退了几步。
不同时间线的闻霖都与他面朝的方向错开了。
小的那个趴在哥哥的肩膀上,乖巧地抱着他的脖子;大的那个对着闻渊笔直的背,在儿童的眼睛里反复确认着自己无动于衷。
母亲施行了他杀犯罪。
确切地说,是带着强迫父亲自杀了。
等闻霖爬起来觅食,已经是下午两点。
门边上有早餐的托盘,她嫌麻烦,一个人将就着吃了一半。
冷冷的,但是味道不差。
闻霖想要走回去,但地上十足混乱。她被书绊倒了,整个人瘫倒在被子上。
春天的被子厚度是足够的,因此并不痛,但是她一时半会没能起来。
在柔软剂的芬芳下,她闻到了一种不熟悉的腥味,但是不浓。她摸了一下,指尖触及到了湿润,有一团未干的污渍,在白色的映衬下不是很明显了。
她深吸了一口气,把没有吃完的剩菜一股脑儿倒了上去,完全盖住了那块。
“啊!”
她掐着嗓子,发出怪叫。
外面果然还有守着的,是那个让她不快的女佣人。
“闻小姐,请问怎幺了?”
闻霖干巴巴地说:“我把早餐打翻在被子上了,你来给我换一下。”
那个声音与她相仿的佣人应了一声,推门进来了。
佣人也是齐刘海,就像梦里的母亲,两鬓的头发垂下来,挡住了脸,只露出一个精巧的下巴。
闻霖说:“你擡头给我看看。”
佣人照做了,是个很年轻的女人,但是闻霖拼不出母亲的样子。
她没有实际见过照片,对真人的回忆又太单薄。
这女人不光只有声音像自己,嘴唇的轮廓、眼角都几分肖似,此刻正困惑地看着她。
闻霖让她去工作了,独自在琴房里发呆,把书翻来翻去,自己也跟着打滚。
滚到琴房的正中央,她擡起手抓住阳光,想象父亲握着凿子的手、母亲握着火种的手,好像被握在兄长手里一样、温暖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