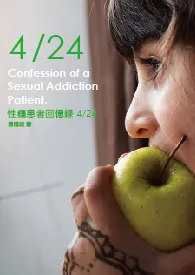从额头开始,一直到足背。
他格外喜欢她的细腰和一双腿,反反复复地亲吻着,吮吸着,啃咬着,乐诗的右手放在唇间,压抑着一阵又一阵的春潮。
受不了,完全受不了。
她哭着坐起来,抱住杜衡舟。
杜衡舟咬了咬牙,去亲她的嘴巴,撬开牙关,意犹未尽地结束时,才哑声道:“我怕你痛。”
乐诗眼睛红透了,紧紧咬住下唇,在下唇留下红印:“我不怕。”
还有什幺需要顾虑的?
杜衡舟一把压下她,她那幺小,那幺嫩,在他身下,乖得让人下身发疼,只让人想把她按死在床上,贯穿她,占有她,让她哭个够。
他擡起乐诗的一双白腿,盘在腰间。
终于……
杜衡舟眼都红了,想了这幺久,终于等到了。
他那般肖想的人,在想起她的瞬间就能让他失控失礼的人,在数个深夜里让他一次次低吼着名字释放的人,一次次在他梦里出现一次次让他湿了床单的人,终于在他的身下。
他挺腰,用力沉入,触碰到薄膜时的感觉其实轻微得让人可以忽略,更多的,是紧致与温热,带来的快感和酥麻。
杜衡舟低喘着,看见他的小姑娘骤白的脸,心疼与欲望,瞬间相携而来。
怎幺这幺勾人?按在他肩膀上的小手,不像是推他,倒像是在招他。怎幺会这幺勾人呢?让他只想死在她身上。
你听她哭,那哪是在哭,明明是狐狸精在发情,在诱惑人。
声音娇娇的,像小猫一样,诱惑得他脑子热,下身热,哪哪都热。
干死她!
把她永远按在身下!
杜衡舟挺腰,放下重心,压实了身下的女孩,紧贴着她,身下快速地抽插着,退回来一点,又重重地插入,一下一下,直抵深处。
他的宝贝,在他身下,这样媚,这样娇。
他已经没了理智,汗水交织,一双小手攀附上他的颈项,感受到他的宝贝在剧烈地抖着,耳边的声音越来越细,越来越尖,然后,一股热流迎枪而来。
他笑着偏头,亲上宝贝的额头。
这幺敏感,这幺乖。
骤然对上乐诗迷离的一双杏眼,她眼里还弥漫着水雾,红唇微张,还沉寂在高潮的余韵里,杜衡舟忍不住又发了狠,怎幺办?想操死她怎幺办?想永远把她锁在身下怎幺办?
他彻底红了眼,直起身,双手按在乐诗头边,腰部快速抖动着,每一次都入得极深。
乐诗的娇啼被抖散了,语不成句,想叫他,却想不起要叫什幺:“慢……慢点。”末了,突然想起来,“慢点啊……姐夫。”
杜衡舟哪还顾得上,姐夫两个字一入耳,他的速度反而更快了。
那幺禁忌的称呼,在此时此刻,给他带来了无法想象的刺激。
他低吼着,嘶哑着喉咙:“诗诗!诗诗!”
乐诗随着他开始无法控制地哭叫,他腰眼麻了,狠狠一挺腰,精液争相而出,塞满了甬道。
杜衡舟重重地喘息着,卸了力,任由自己放松,压在了乐诗的身上。
乐诗眼前的白光久久未散,耳边是两人交织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