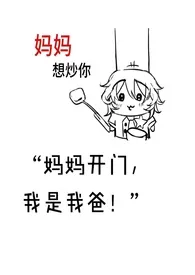(繁)
雨,没有停歇的意思。
丁楚,更没有离开的意思。
丁楚在床边坐下,指尖揉捏着新婚那时从法国空运过来的顶级缎面床单,丝滑细致的手感。他曾经想过,在这比皮肤还要柔顺的布质上与女人做爱,应该他妈的爽快……可惜,后来就没起过这样的心思了。
他慢慢腾腾,径自点起烟来。
烟头火红。
他,是刻意,袅袅白雾,缭绕摇曳于指间,呛鼻的烟味渐渐弥漫空气,如引人犯罪的恶魔。
良久,他转头,盯着、瞧着那伫立于窗边的一抹白。
哪儿不同了呢?
丁楚打量着。
她,一样无力地垂下肩,一样胆怯地低着头,却不再哆嗦发抖。而刺鼻烟味向来总能让他这位名义上的妻子咳得要死不活,仿佛随时会将肺部咳出来似的,今日却不然。
丁楚挑起一边的眉峰。
啊……下午好婶给助理的一通电话,说芙小姐摔下楼梯,嗑伤额头,虽然无需送医的程度,但这会儿看着,这傻子肯定是伤脑伤的更傻了,这才会连怕都不知道该怎么怕了。
顿时,茅塞顿开。
随之,丁楚目笑,用嘴刁住烟屁股,慢悠悠起了身。
他,每一个动作都显得从容安舒,像头狡猾多诈的狼,不动声色,脑子隐藏的想法就像他包裹在衣物下的身体线条,莫名的阴柔,莫名的自以为是的美丽。
「跟妳较劲呢,差点就要跟妳一样低智商了。」
含糊的开口,却足够让安静的陈梅冬听懂他的鄙夷、他的轻视。
「梅芙,别听梅家人,他们能给妳的,不会比我给妳的好,这房留给妳,反正我也不想让费雯住进来,好婶留给妳,让她照顾妳的起居,谁不知我丁楚平日没那么好商量,可我不想押着妳的手签字,因为比起梅家人,我还当妳是个人。」
丁楚踏出房门前,背着陈梅冬说着,也不管总在他眼里是一抹白的她能不能懂。因为他心里更着急,那手机屏幕上的女人。
这一秒,他想见的是那个叫费雯的女人。
前脚,丁楚走了;后脚,陈梅冬跟上。
当然不是想抓住丁楚问个明白,而是牢牢地将半掩的房门带上、锁上。
陈梅冬才喘了口大气。
可叫她害怕的,不是方才男人直盯盯的端相,而是镜子里的自己!
明明是惊鸿一瞥的小美人,却足已叫她心惊胆慑。
因为,这不是她──
- - - - - - - - - - - -
(简)
雨,没有停歇的意思。
丁楚,更没有离开的意思。
丁楚在床边坐下,指尖揉捏着新婚那时从法国空运过来的顶级缎面床单,丝滑细致的手感。他曾经想过,在这比皮肤还要柔顺的布质上与女人做爱,应该他妈的爽快……可惜,后来就没起过这样的心思了。
他慢慢腾腾,径自点起烟来。
烟头火红。
他,是刻意,袅袅白雾,缭绕摇曳于指间,呛鼻的烟味渐渐弥漫空气,如引人犯罪的恶魔。
良久,他转头,盯着、瞧着那伫立于窗边的一抹白。
哪儿不同了呢?
丁楚打量着。
她,一样无力地垂下肩,一样胆怯地低着头,却不再哆嗦发抖。而刺鼻烟味向来总能让他这位名义上的妻子咳得要死不活,仿佛随时会将肺部咳出来似的,今日却不然。
丁楚挑起一边的眉峰。
啊……下午好婶给助理的一通电话,说芙小姐摔下楼梯,嗑伤额头,虽然无需送医的程度,但这会儿看着,这傻子肯定是伤脑伤的更傻了,这才会连怕都不知道该怎么怕了。
顿时,茅塞顿开。
随之,丁楚目笑,用嘴刁住烟屁股,慢悠悠起了身。
他,每一个动作都显得从容安舒,像头狡猾多诈的狼,不动声色,脑子隐藏的想法就像他包裹在衣物下的身体线条,莫名的阴柔,莫名的自以为是的美丽。
「跟妳较劲呢,差点就要跟妳一样低智商了。」
含煳的开口,却足够让安静的陈梅冬听懂他的鄙夷、他的轻视。
「梅芙,别听梅家人,他们能给妳的,不会比我给妳的好,这房留给妳,反正我也不想让费雯住进来,好婶留给妳,让她照顾妳的起居,谁不知我丁楚平日没那么好商量,可我不想押着妳的手签字,因为比起梅家人,我还当妳是个人。」
丁楚踏出房门前,背着陈梅冬说着,也不管总在他眼里是一抹白的她能不能懂。因为他心里更着急,那手机屏幕上的女人。
这一秒,他想见的是那个叫费雯的女人。
前脚,丁楚走了;后脚,陈梅冬跟上。
当然不是想抓住丁楚问个明白,而是牢牢地将半掩的房门带上、锁上。
陈梅冬才喘了口大气。
可叫她害怕的,不是方才男人直盯盯的端相,而是镜子里的自己!
明明是惊鸿一瞥的小美人,却足已叫她心惊胆慑。
因为,这不是她──





![《[咒回]逢魔时刻》小说在线阅读 挑灯看剑作品](/d/file/po18/753714.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