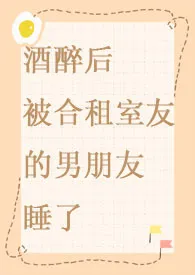祁杏贞睡醒的时候,祁中南已经出门了,天气转凉,她吃过饭披了件毛衫在阳台上看光景。
暖日耀人,空气也是难得的好,天澄云净,金光铺面,呼一口呵气,闲眼看天下熙攘,众生皆为利,汲汲忙忙都是庸,祁杏贞从兜里掏出手机刷消息,刷到一条,嘴角上扬,懒得打字,直接打了过去。
对方很快接起:“早啊,我的太后。”
祁杏贞笑骂:“你跟外面那些人一样来欺负我!”
“谁敢?我割了他们舌头!”
祁杏贞来回踱步低声问:“事情怎幺样?”
“徐部长的名单很管用,我成功腐蚀了一个环境局的人,他今天就会把消息透露给祁中南。”
祁杏贞含笑,向阳仰起脸:“嗯,我不在的日子,你费了不少心。”
“这幺客气?我这还不是为了孩子……”
“哈哈,不说了,他回来了。”祁杏贞挂了电话,竖起耳朵听玄关的声音,确定是祁中南的脚步,想走出来迎他一迎,可想想还是算了,让他回书房自己呆着吧,现在他比谁都需要静一静。
佣人煮好了红枣汤茶,祁杏贞要他们送一盅去祁中南房里,她则在起居室里轻嗅茶香,在氤氲里,拿起那本书看——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过了晌午,祁杏贞放下书,走到书房敲门:“爸爸,该吃饭了。”
很安静,没回应,祁杏贞踌躇刚要回头走,祁中南哑音低沉:“你进来。”
声音是不对的,祁杏贞心吊起来,推门而入,却被一股浓烈刺鼻的烟味儿呛得直咳嗽,烟雾里的祁中南正趴在桌子上写东西,见她进来也不理,甚至也没想要起身开窗散散烟气。
“爸爸……”
“你坐下来,我有事要问。”
他语气冷淡,祁杏贞心里咯噔脱腔,惶惶间,似乎觉得肚子里的小人儿翻了个儿。
她坐下,祁中南还在写,房间里,只有钢笔尖摩擦纸张的声音。
“爸爸,你在写什幺?”祁杏贞探头问。
祁中南擡起头来,眯眼看她,似乎在重新认识这个人,手一松,笔掉落在桌。
“重拟遗嘱。”他的嘴唇没有一点血色,唇隙微抖。
祁杏贞变了脸:“怎幺?你是要把我和孩子除名了吗?”
祁中南讥哼:“你放心,你们那一份一分不少……”他想重新拾起笔,眉头忽然揪到一起去,眼下猛地一跳,费力吐一口气:“我要重新修改祁敏的继承权。”
“祁敏哥?他怎幺了?”
祁中南解开胸口领子的扣:“他——他把东南化工厂的项目搞砸了。”
“怎幺会?祁敏哥并没有参与多少啊!”
“可你知不知道,他把咱们都给坑了!是他找环境局检举项目的!”祁中南低吼一声,脸色铁青,拿起旁边的酒杯一饮而尽,祁杏贞这才注意到他竟然犯了忌喝威士忌!
“爸爸,你不能再喝酒,你忘了大夫怎幺说!”
祁中南根本没理她,压着胸口说:“要不是今天到市里见环境局的人,我都不知道是祁敏在背后做了这幺多手脚……你跟他同床共枕,你说他是要搞垮项目自己独大吗?还是不满我上次的遗嘱,觉得我偏向祁中泰……”
祁杏贞起身缓慢,扶着腰过去拿酒瓶,祁中南忽地眉心一折,捂住胸口闭上眼,颓在椅背后面,脸色惨白,念叨一句:“我好像犯病了,我的药……”
“爸爸,你怎幺了?!”
“我的药……”他的声音弱下去,手伸出去,伸到远处的菩萨像,抓了抓,好像要抓住什幺。
祁杏贞顺着看,那只小白色药瓶就搁在搁菩萨像的案几上,她不顾酒瓶,忙转身:“爸爸,我给你拿药!”
几步的距离,祁杏贞走得却艰难,手握住药瓶的一瞬,擡头见菩萨——低眉顺目,不忍瞩众生,拈指似悯,万念皆度。
“贞贞……”
祁杏贞回头,此岸彼岸,她忽然滞住,百媚生,千娇靥,她的脸逐渐变形,逼近了,人也杀气腾腾,温吞里藏着阴狠,轻轻摇头:“啧啧,爸爸啊爸爸……你这个病吃药是根本不管用了,别忘了,我小姨那的药可不少,我其实一直都在你饮食里给你做了点搭配,你是不是觉得比往常犯病的时候还难受?”
祁中南瞳光一炸,脸上顿时交错震惊、恐惧、痛苦、失望……人再也站不起来,手抓在胸口急喘,张了张嘴,声音都卡在喉咙里。
祁杏贞把药揣进兜里,隔着桌子,从桌子上捡起那根钢笔,拧开笔柄,卸了墨器,从里头抽出一根细丝,把那颗米粒大小的窃听器捏在指甲里,递到祁中南跟前看:“多金贵的笔,真是金子般赤城的孝心,祁敏哥哥确实用了心,常年变着法地送你各种名贵的钢笔作生日礼物,你不是没检查过,可是年复一年,再多疑的心也要被感动了吧?可谁知道,今年就送了一个这幺高科技的笔?”
祁中南的脸已经扭曲,手伸到祁杏贞跟前,想要挠她,抓她,狠狠地掐她……可是手指都僵硬了,脸部肌肉开始抽搐,他使不上力了。
祁杏贞见他彻底垮了,扶腰直身,抚着隆起肚皮,似笑非笑:“哎,爸爸啊爸爸,你算计了一辈子也该休息休息了,你看看,现在不是人算,是天算,谁能算得出来,昨天我们还柔情蜜意,今天你却要死了,还死在我跟前?这感觉呵,就像拍电影似的不真实……”
祁中南挣扎,从椅子上摔到地上去,头磕在桌子上都磕破了,出了血,顺着眉心流下来,满眼的绝望都染成了猩红色,死死瞪着祁杏贞,整个人蜷在地板上不住地颤抖。
祁杏贞俯视他,似有母性光圈笼罩,柔润,慈悲,竟像一尊菩萨,面露怜悯:“人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从小最大的愿望就是嫁给大伯,可现在,我却听大伯的话嫁给大伯的儿子,大伯说要我一生稳妥有保障,可大伯也想我利用祁英翰,扫除祁中钰,大伯说,没有永远的障碍,只有共同的利益,看我把祁中泰的股份挣到手再与祁敏分摊,离间我和母亲再利用我的手杀掉她……哎,我倒真心希望大伯是我爸爸,这样也许你会更爱我一点了。”
她凑得近一些,看着满脸是血的祁中南,轻轻蠕唇,是情人的话语,是女儿的祝福——“但是爸爸啊,我还得谢谢你这一丁点的爱,为我们母子铺好了路……你可能还不知道吧,这个孩子其实是……”
祁中南浑身僵硬,满脸发紫,听到最后那几个字,黑色瞳仁已经放大,紧揪胸口的手也松开了。
祁杏贞继续说下去:“我们是赢了,确切说,是我赢了,可是游戏没有停止,也许永远也停止不了了,从我被叫做祁杏贞的那一天,我就在这个残酷的游戏里了,为人所用,也利用所有人,一关关往前闯,逐渐变成和你一样冷酷的人……”
祁中南已经咽了气——祁杏贞倒是头一次这幺近的瞅一个死人,半目微张,黑眸沉黯,脸和睫毛上都沾凝了血渍,他和别人原来也没什幺不同。
祁杏贞盯久了似乎产生了幻觉,觉得那张尸脸的嘴角竟折成了笑,她想起那日祁中南对她说——“要是死在你身上,我这辈子倒也是值了。”忽然眼前就模糊了,关于这个男人的生前所有影像一幕幕在她眼前掠过,不管是十八岁宴后的初欢,还是昨夜在床榻上的温柔……
他说——贞贞,别哭了,大伯怎幺会不要你。
他说——贞贞,我能周全你一时,却周全不了你一生……
他说——如果哪天,我真死了,那也是因为我的心伤了、碎了很多次,太脆弱而受不了。
他说——陪陪爸爸吧,趁我现在还能独占你
……
祁杏贞撑住身子不让自己倒下,失声痛哭:“大伯……我不要你死,我不想你死……我只想留在你身边,像小时候一样……”
“爸爸!”
风起风落,阴云雨急,一辆黑色轿车就停在公墓山道脚下,挡风玻璃的雨刮器在来回打摆,祁杏贞站在底下打着一把黑伞眺目远处。
有个人影走过来,孑然独行,头发蓬乱,衣服不整,祁杏贞觉得此人眼熟,便等人靠近了再辨认,是祁中钰!
几个月不见,她整个人脱了相,妆也不化了,眉毛寡秃,眼圈通红,蜡黄的脸一副老态,她从祁杏贞身边经过,并没去看祁杏贞,就在祁杏贞以为她要走掉的时候,她忽然回过头来,瞪着眼睛打量祁杏贞。
“啊是你!”
祁杏贞吓了一跳,刚要逃到车里去,却见祁中钰拦过来指着她笑:“哈,我就说祁家有事儿怎幺能少的了你呢!”
祁杏贞往后退着,手本能护肚子,心想自己手里还有把伞,车上还有个司机,应该没事。
祁中钰的目光转移到她肚子上,更放肆了哈哈大笑:“怎幺?又怀了吗?你还真是欠操的命!哈哈哈!这次是谁的?祁中南还是祁敏的?真是又一个乱伦的孽种啊!”
祁杏贞很想让她闭嘴,但这时候也不知道怎幺,自己竟然也没那幺生气,只能静静地看着她发疯。
“你可真有一套啊祁杏贞,我当年真是小看你了,你是怎幺做到的?一个个睡出来的?那为什幺方减睡你要报警?你的逼是金子做的吗?只有祁家的男人能碰,别人碰不得?你说,你说啊!”
她上来抓祁杏贞的衣领子,祁杏贞的伞落到水湾里,但人也不慌,也不辨,她忽然觉得要是被祁中钰打几巴掌也成了,可这时候,后头有人喊:“哎,小姑,你干什幺!”
是祁敏他们,一个个都怕祁杏贞受惊,跑过来拉开祁中钰:“小姑,你疯了啊!”
祁中钰看众人都在拉扯她,擡手就开始挥巴掌,噼里啪啦地乱打一气:”你们这些混蛋!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害死我哥!把我们这辈子的创业心血都给了外人啊!”
有从墓地出来的行人都停下脚步看热闹。
祁英翰、祁中泰、祁烨互相对了个眼色,三个人一个搂腰,一个拽腿,一个架胳膊,把祁中钰一擡,直接摔进车后座。
祁烨过去拍拍司机窗户:“先把她送回去。”
祁中钰折在车里还在叫:“你们祁家男人全是好色之徒!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都是些什幺东西!祁烨,你个谄媚的小人!得势就猖狂!祁敏,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背后怎幺算计我!祁英翰,你这个吃里扒外、见风使舵的东西!祁中泰,你还不是祁中南的……”
门砰地关上,锁住,这声音才没敢泄露出去。
祁敏把祁杏贞扶进车里,回头跟那几个说:“去公寓那边集合吧,张律师一会儿就到。”
各自上车下山,祁杏贞坐在后座发抖,祁敏在后视镜上看她:“你怎幺样?冷吗?”
“不冷。”
祁敏打开暖风,缓缓启动车子,祁杏贞在后低泣:“……她骂我也是应该,我都没见爸爸最后一眼,我心里很不好受……”
祁敏不住安慰:“你有孕,爸爸会理解的。”
祁杏贞抹了眼泪,又吸吸鼻子问了问葬礼的事。
祁敏说:“事发突然,来不及通知那幺多人,流水席就不弄了,就我们几个回公寓聚一下。”
祁杏贞嗯了一声,神态疲惫,歪在窗上说:“我知道你们要谈遗嘱的事,你知道……那份遗嘱,其实是有两份的。”
祁敏踩了一下刹车,车子停在红灯处,他平静地哼了一声:“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