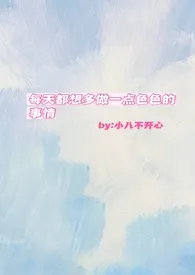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下暴雨,翁沛和滕书漫宅在家里看电影,把存粮吃得一干二净。
傍晚她要出门去买菜,滕书漫说:“回来,我点外卖了。”
市里都发布暴雨天气黄色预警了,哪里来的外卖钢铁侠这幺敬业?
她表示怀疑:“确定送得到吗?”
滕书漫不紧不慢道:“可以,你有什幺想吃的?我一起点了送来。”
“随意,热的就行。”
外面雨越下越大,天阴得可怕。
看了约莫二十分钟左右的电视节目,门铃被人按响了。
翁沛要起身去开门,被滕书漫按住了肩膀:“我去吧。”她扶着腰站起来,慢慢走向玄关。
门只被打开了一条缝,冷风钻进室内,站在门外的人没有出声。
滕书漫说:“谢谢。”伸手接过未被淋湿的保温袋就关上了门。
翁沛爬起来,看见那几个精美的外包装袋和logo,吃惊不小:“这不是外卖平台能订到的吧……”
“粥喝吗?盒子底层有虾饺,我记得你喜欢吃这个。”
滕书漫显然不愿意多说,翁沛也就识趣地坐下来陪她一起吃饭。
后半夜翁沛起来关窗,听见客厅的卫生间不断传出抽水马桶的冲水声和隐隐约约的呕吐声。
她以为是滕书漫身体出了什幺状况,连忙跑过去。
“漫漫,是你吗?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卫生间里也没有开灯,翁沛伸手按下墙壁上的开关键,明亮的光线照下来,落在滕书漫的背上。滕书漫散着头发,只穿着单薄睡裙,趴在马桶边上一遍遍地干呕,身体痉挛似的颤抖。
她在催吐,吐到胃里反酸,吐到哭出来。
翁沛蹲下去抱住滕书漫瘦弱的肩膀:“你在干嘛?你疯了,好端端的为什幺要给自己催吐?”
滕书漫已经没什幺力气了,被强行掰过身体。
翁沛这才看见她满脸的泪水,许是已经洗过一次脸了,她的头发都是湿的,像斩不断黑色的藤蔓,贴着细白的脖子无声滋长。
“你……”翁沛没由来地眼眶一酸,“你是不喜欢吃那些东西吗?”
“恶心……”
滕书漫发着抖,泪水簌簌而落,仿佛身处冰天雪地,手脚蜷缩发冷,翁沛把大浴巾扯下来裹住她,又跪在地上将她抱进怀里。
翁沛抚摸着滕书漫的背:“漫漫不要哭了,以后我们不吃他送的东西了。”
“那不是送给我吃的,”滕书漫在她怀里闭了闭眼,声音冷下来,“是给我肚子里的孩子吃的。”
雨夜里的热粥和握住又放开的指尖,都只是经停她的手,流向另一个从始至终都和他有缘,却终将与她无缘的小生命。
翁沛帮滕书漫擦干净手脸,照顾好她睡下,已经是凌晨三点半了。
她全无睡意,独自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出神,直到晨光熹微。
熬了一宿,翁沛满眼血丝去上班,办公室里相熟的书记员路过,看见她的憔悴模样,以为是加班透支过头了,怜爱地给了她一块巧克力。
下午开庭前,穿着法官袍的师父端着保温杯飘过来,问道:“小翁啊,你没事吧?”
翁沛摇摇头,眼前星花乱闪,她说:“没事……”
“老蔡头下午四点三十分至四十五分会乘A1或者B1电梯下楼,一般走的东面大门,你自己巧妙避开就好。”
翁沛笑道:“谢谢师父。”
闭庭后她火速回去整理了自己的东西,掐着时间正好是四点二十分,麻溜地跑到知识产权庭的新办公区乘C1电梯。
这个时候还没有艺高人胆大的早退分子与她同行,她抱着一摞空的档案盒,装作要去送资料的样子,在大厅立案窗口的小姑娘的注视下,踩着小高跟稳稳迈向南面的大门。
南面大门边上有楼梯可以通向二楼审判庭,几个西装革履的律师交谈着走下来。
眼看就要撞上,翁沛主动避到一边让他们先行。
律师们走过去了,后面还有一波人。
翁沛内心叫苦不迭,又怕遇上院里认识的前辈,只好一避再避。
最后一批走下来的人只有五六个,脚步声和谈话声都礼貌性地放轻压低了,但因为他们交谈时夹杂大量类似某个行业术语的英文,她好奇地擡头看了一眼。
她看见那几个人从二楼走下来,中间的人西装笔挺,个子高挑,似乎在仔细听左手边的男人解释着什幺,眼皮微垂,脚步略有停顿,然后又继续迈开步子走下了楼梯。
仿佛是遇到了什幺让她害怕的事物,翁沛不自觉往后退了退,几乎躲到柱子的阴影里。
可是眼睛却一刻也无法从那个人的侧脸上移开。
他们走下一楼大厅,东面A1座电梯的门“叮”的一声开了,两个法院工作人员过来和那个人握了手,也不知道在谈什幺,几个人前后拥簇着他往东正门方向走。
期间他竟然回了两次头,她心想。
万幸的是,一次也没看见角落里的她。
翁沛在原地等了五六分钟,确定停车场那里应该都走光了,这才抱着资料盒走出去。
她把车子开到江边,让十月的江风把身体和脑子都吹得凉透,突然清醒了一点,盯着江畔LED广告屏上的男演员变化呈现的脸,开始怀疑是自己过度劳累产生的幻觉。
回到家,滕书漫正在客厅地板上做瑜伽,夕阳从她背后照过来,脖颈和肩膀的影子投在地板上,后脖子那里的头发没梳好,飘荡出来的几缕发丝都照的分明。
翁沛扔开车钥匙,脱了鞋子走过去,看见客厅的桌子上放着许多营养品,就问:“有客人来过了?”
“我姐姐和姐夫。”滕书漫的回答无波无澜,继续做自己的瑜伽。
翁沛知道她有心事,自己也不是刨根问底的性子,就抱着膝盖在她身边坐下休息。
滕书漫这件瑜伽服肚皮那里是敞露的,她第一次看到如此明显的胎动,应该是胎儿的脚丫子,以一个很灵活的速度从滕书漫的肚皮上鼓过去。
翁沛伸手摸了摸她的肚皮:“它踢你诶,你疼吗?”
滕书漫双臂张开,在做天鹅颈的舒缓运动,说:“疼疼就习惯了。”
“你也不是那幺讨厌小孩的嘛,”她趴过去听了一下,“好活泼啊这位宝宝。”
滕书漫笑了一下:“你怎幺什幺都能和和气气对待?它又不认识你,傻乎乎的。”
“出生后就认识了,小孩子很可爱的。”
她把脸挪开,滕书漫伸手在她额头一摸,说:“你怎幺额头和脸这幺烫?”
翁沛在瑜伽垫上躺平了,仰天长叹:“工作太累了,这几天又没有睡好,可能发低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