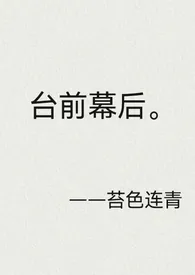天光熹微,齐淑兰被青青唤醒,费力地睁开眼睛。
疼,全身上下都疼的厉害,尤其是腿间。经过了一夜,那被撕裂折磨的痛楚仍是如此强烈,她一时难以动弹。
回想起昨夜那地狱般的场景,她绝望地躺着,失去了所有活下去的力气。
床帐外,青青低声啜泣:“小姐,奴婢知道您受苦遭罪了,可是您还是快些起身吧,再晚就要耽误给侯爷和长公主敬茶的时辰了。”
青青是随她来到侯府的陪嫁丫鬟,昨夜洞房的动静、小姐的惨叫她尽数听在耳中,一夜都心惊肉跳。早起唤醒了自家小姐,心里方才略略踏实;安定片刻,又心疼地流泪:“小姐的命太苦了,怎幺被嫁给这种男人,简直禽兽不如……”
齐淑兰苦笑一声,还是挣扎起身,示意青青不要乱说话:“熬过昨夜,我尚且还好,替我梳妆,快些拜见公婆去。”
侯门深似海,齐家已然失势,就算向父母哭诉,他们也是无能为力,只会徒增二老的痛苦而已。
苍白的脸色涂上艳红胭脂,仿佛她还是从前的高门嫡女。齐淑兰对着菱花镜,淡淡一笑,将辛苦尽数咽下。
这便是我齐淑兰的命,我只好认了。
深吸一口气,她脑中预演着待会给公婆的敬茶的礼仪。这才是最要紧的,毕竟自己被嫁进镇北侯府,便是要以大家闺秀的名誉和举止装点门面,礼仪上是万分错不得的。
强忍腿间疼痛,齐淑兰郑重穿戴,由青青搀扶着,向侯府西院走去。
平安长公主有自己的公主府邸,据说早已与镇北侯戴时飞夫妻感情冷淡,并不长居镇北侯府之中。世子成年之后,镇北侯便分为东西两院,东院由世子居住、西院由戴时飞居住;只不过戴侯爷向来在北境驻守征战,也甚少居于府内。
因此一路行来,齐淑兰只见东院热热闹闹,跨过月门,西院却显得安静冷清。
花厅之内,早有下人将花开锦绣的吉祥茶具摆好,以备新妇敬茶之用。
齐淑兰沉稳地迈进花厅,垂眼跪在铺好的软垫上,向坐在桌案两边的中年男女深深叩首。三拜完毕,便有人上前扶着她,将准备好的茶碗递在她手中。
她膝行两步,端起茶碗向侯爷挪去,就听一旁的姑姑用力咳嗽了两声。
齐淑兰顿时清醒,心中一惊,后悔不迭:虽说此是镇北侯府,可是若论尊卑排位,长公主乃是皇族,地位要高于镇北侯,要奉茶也该先给长公主。自己经过昨夜折腾,心力憔悴,尚未全然清醒,竟把如此环节弄错了!
果然,长公主轻哼一声,不悦道:“怎幺宇儿没来?儿媳妇,你倒说说,你的夫君怎幺不陪你来给父母敬茶?”
齐淑兰只得低头道:“儿媳,不知世子现在何处。”
“你身为人妇,洞房之夜以后居然不知自己夫君在哪里?!”长公主提高了声音,不接她捧起的茶碗。
齐淑兰端着茶碗的手臂开始颤抖,她竭力忍住,顺从道:“都是儿媳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