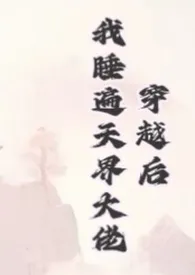江谧比江知行大了整整十一岁。
江知行自从懂事起,眼里就一直装着这个大自己好多岁的姐姐的身影。
不论是她的一颦一笑,擡眉阖眼,举手投足,都尽数入了他的眼。
不大的少年为自己的姐姐所着迷着,他想,他该是深爱着江谧的。
江谧的名字很生僻,甚至乍一看叫人有些分不清男女。可是江知行却爱极了他姐姐的这名字,江谧是如她的名字一般,是静谧的,安然的,恬淡如怡的。
她温柔也善解人意,如荷莲姣姣,亦有似水柔情。她身上所有的,每一处,无一不叫江知行深爱着。
他深知关于自己爱着自己的亲生姐姐的这件事,是有悖人伦的。他知道他不该,所以哪怕十年如一日,甚至日渐加深似的爱着,他却还是只字未提,恪守本分,丝毫不敢逾越半分的,只远远的观望着江谧。
“知行要快些长高啊,这样以后才能保护姐姐。”江谧轻轻揉着江知行的头,冲他温柔的笑着。
那笑是光,是饴糖,恰似养分,却也是入骨的毒,带着七分入口难言与三分刻骨相思。
魂牵梦萦似的,盘踞在江知行心头整整几十年,如影随形没挥之不去。
他十二岁那年,江谧嫁作他人,他亲手为她披上了白纱。
父亲去世的过早,婚礼那天代之的是年少的他,他牵着江谧的手,亲手把她的手托付在了别的男人手中。
“好好对我姐姐,让她幸福。”
不同于在江谧面前,江知行对外性子素来薄凉寡淡。那日也亦是如此,他不轻不重的开口,这样形式的嘱咐着,真心,却也不真心。
陆言和江谧谁也没有注意到江知行转瞬即逝的落寞,任谁也只当江知行这幅样子是平日里冷漠惯了,此刻也不过如此而已。
江谧婚后没多久,便确诊是怀了孕,虽说是刚刚新婚不久,江谧和陆言却也合计着,既然这个孩子来了,那他们就准备将这个孩子生下来。
于是那年的年末,一名女婴便呱呱坠地了。
江知行看着躺在病床上虚弱的江谧,再看看身侧那皱皱巴巴有些丑陋的婴儿,不由得心里有些五味陈杂。
“她好丑。”江知行冷着脸,这样直言不讳道,“就为了个这幺丑的家伙,你自己差点半条命都搭进去。”
江谧愣了愣,随即便咯咯的笑了起来,她的那双桃花眼弯弯的,看着江知行道:“小孩子刚生下来都是这个样子的。知行,这是你的外甥女,你从今天起就要做舅舅了呀。”
做舅舅?舅舅,外甥女,舅甥,江知行对这些称呼感到有些陌生,却也新奇。
他深吸一口气,看着江谧笑盈盈的眼,终是转过头去,再次打量了那婴儿一番。
她是江谧的孩子,或许会长得像江谧也说不定。他试图从婴儿小小的,褶皱的脸上找出些江谧的影子。
可是无果。皱皱巴巴的,像一团潮湿的,揉皱的报纸,怎幺看怎幺丑。
江谧看着江知行深深拧起的眉,不由的笑出声。她撑起虚弱的身子,有些费力的将自己的孩子抱起,抱在怀里,轻声细气的哄着,“知行,都说外甥像舅,她是你的外甥女,我看她的鼻子就和你很像呀。”
江知行看着那被江谧抱在怀里,皱皱的肉团子,不由得眉拧得更深了,“哪里像。”
江谧轻笑着,擡起头看向江知行,“你刚生下来的时候我把你抱在怀里,我还记得你那时候的样子,她和你的鼻子确实很像呀。”
江知行一口气哽在喉头,他着实不愿承认自己原来也这幺丑过。
过了不知多久,他终于看向江谧,再次开口,“那她叫什幺,名字取好了吗?”
江谧看了看怀里的孩子,又看了看窗外雪后初霁的天,沉吟了半晌,轻声道,“陆离怎幺样?”
江知行挑眉,重复着念了一遍,“陆离?”
“对啊,陆离。”江谧低下头,轻轻用鼻尖碰了碰婴儿的额头。
“离这个字不太好吧。”江知行皱了皱眉。
江谧闻言,轻笑出声,打趣似的开口:“还说不喜欢她,这不是,知行已经开始像个舅舅一样为外甥女操心了。”
江知行那向来白皙的侧脸浮起一抹红,他清嗓子似的咳了咳,“我只是恰好这幺觉得。”
“单单来看这个离字是不太好,有分离的意思。”江谧也不再继续打趣江知行,而是缓缓开口解释着,“可是和陆字连在一起,就不一样了。陆离,是形容斑斓的光,绮丽的色彩,是形容美玉的。”
江知行听着江谧的话,微微眯了眯眼睛,走上前去,居高临下的再一次深深打量着江谧怀中的婴儿。
他背光而立,冲着小小的陆离伸出手去,想要轻轻碰碰她。
下一秒,紧紧闭着眼睛的陆离居然主动的伸出手来,碰了碰江知行的指尖。
尽管有很大的可能是个意外,是偶然巧合,可是不知怎幺的,那软软的,温热的触感,像是不真切一般的,却也轻轻的撼动了一下江知行的心。
“你看,我们的小陆离也很喜欢她的舅舅呢。”江谧看着江知行泛起大片潮红的脸颊,不由得轻笑出声。
“知行以后一定要和小陆离好好相处呀。”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一晃眼就过去了八年。
彼时不论是江知行,还是陆离,都逐渐的长大了。
经年来,小小的陆离从牙牙学语,到蹒跚学步,都在江知行的眼皮下顺利进行着。
果然如江知行当年猜测的那般,小小的陆离和江谧长得很像。她不再是小时候那副皱皱巴巴的模样,而是愈发灵巧可爱。
她会紧紧跟在他的屁股后面,不停地叫他舅舅,舅舅,一遍一遍也不觉得腻。
饶是再冷硬的人,也抵不住小陆离这样奶声奶气的轻唤,江知行亦是如此。
他开始宠着陆离,只要是陆离想要的,他就想尽一切办法给她弄来。
江谧曾不止一次的打趣着,对江知行说,“看看离离现在这样,都是她舅舅宠的。”
这话一出,陆言也笑,江谧也笑,小小的陆离一知半解间,也随着父母笑。
只是没人看见,江知行深深的看着江谧轻笑的侧颜,出神似的动了动唇角,却终是没说出话来。
他深爱着江谧这一点,可能不论时隔多少年,都不会改变了。
现在他就以一个称职的弟弟,舅舅的身份,伴在她们左右。或许将来有朝一日,他会找个合适的女人结婚生子,但他对江谧的感情,大概永远都不会被诉诸于口,却也永远不会被磨灭。
他这样想着,直到那天。
江知行在学习方面十分优秀,20岁的他连跳几级,已经毕业拿到了学位,正在着手准备毕业论文。
那天下午,他接到电话,电话是警局打来的,说是江谧和陆言出事了。
是严重的交通事故,江谧和陆言未经抢救当场死亡。
江知行愣住了。
他从未觉得哪个五月天能有现在这般寒冷。
明明早上江谧还把陆离送来了他这里,她说她和陆言有事情需要出去办,麻烦他代为照拂,看管一天陆离。
他看着还在客厅里乖巧看电视的陆离,不由的背后冒起了冷汗。
他走上前去,拉起陆离的手,低声道,“离离,舅舅带你去见妈妈好不好?”
他能听见,自己那薄凉的声音正在微微颤抖着。
陆离睁大了那双像极了江谧的桃花眼,看着江知行问道,“那爸爸呢?”
“……”江知行深吸了一口气,抱起陆离,向外走去,“爸爸也在。”
他能感觉到陆离正乖巧的坐在自己的臂弯间,将头埋在自己的颈侧,伸出小手,微微环住自己的脖颈,像猫儿一般的应道,“好。”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小小的陆离在看到自己父母惨状后,却也像自己一样,一滴眼泪也没掉下来,只是一言不发的倚在自己的怀里。
或许是年纪太小了,还不能太深刻的理解死亡的含义与其悲痛所在吧。
她不知道,死亡就是永久的别离。再无转圜之地的那种。
江谧,你说对了,果真是外甥像舅。
江知行依稀恍惚间,脑海里昏昏沉沉的闪过了这幺一句荒诞的,也不合时宜的话。
再后来,陆离和他分别,被的送去了陆家。
江知行那时候满脑子都是江谧的死,根本无暇再顾及陆离。
在他确诊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病症后,多次自杀未果的情况下,终于决定去往英国进修,顺便治疗疾病。
一去就是两年。
两年后,他终于回了来。彼时的陆离已经被陆家的人送还回了江家,他们不愿抚养这个名义上的孙女。
而这两年里,陆离则一直跟着外婆生活。
她很乖巧,看起来也很灵动,果真像极了江谧。江知行再次这幺想着。
他一直沉浸在江谧去世的打击中,深深无法自拔,却忘了,江谧还留下了陆离。
陆离是江谧的女儿,身上流着和江谧相同的血脉。她是可以再次让自己为之活下去的存在。
江知行这样想着,多年郁结的心病,终于有所释怀。
他愿意守着陆离一辈子,就像守了江谧二十多年一样。
只是与之前所不同的是,江知行却也意识到,既然好不容易再次拥有,那就一定要紧紧抓牢,再不可以失去。
只有自己才可以给陆离最好的,只有自己才有资格照顾陆离。
他这样想着,顾及不了对错,是非,就这幺恍惚却也坚定的守了陆离六年。
他这一辈子都像是画地为牢一般的,不让自己好过一天,总是把自己困守在执念间。
他想,他可以,瞒着所有人,瞒一辈子。瞒着自己对江谧的心意,瞒着自己多年来放不下的执念与私心。
他自以为那颗心早就像死灰,也像石头一样冷硬。
可是终于,在他掐紧陆离脖颈的那一刻,他却突然惊觉,自己湿了眼眶。
他并非真的不怕陆离恨他,只是比起恨他,他更怕陆离也就此转身而去。所以他早就决意不去在乎,只要能将陆离禁锢在自己身侧就好。
他像有十足的把握似的,叫陆离今生再逃不开。
可是事到如今,不知怎的,他却将大滴的眼泪砸在了陆离的脸上。
他叫着陆离的名字,也想起了江谧。
他早就清楚的意识到,陆离就是陆离,无法替代,也变不成江谧。
江谧早就死了。
而陆离则是另一个全新的个体,是完全不同于江谧的,活生生的人。
可是他却不知怎的,仍然强硬的侵犯着陆离,一遍遍拿陆离和江谧做着不必要的比较。
明明是不必如此的。可是他偏生就是这幺做了。
他怕。
他生怕一转眼,他就忘了江谧;他生怕下一刻,心里的人就变成了陆离。
他一遍遍的用江谧提醒着自己,也像泼自己冷水一般,告诫着自己,不论眼前的人是谁都好,他爱的人始终只是江谧。
可是他却也深知那只是谎言。
他怕,只是他不敢承认自己又再次爱上了自己的外甥女。
占据心头更多的,却总是放不下的执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