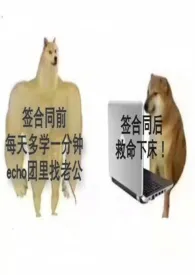凌晨微微暗天色,将整个别墅笼罩在一片朦胧中,让白日所有清醒思绪都变得不再重要。
二十多岁男女,肢体交缠间,彼此都能听到对方快要跳出胸膛心跳声,杭爽被他握住一双手腕按在头顶上方,铺天盖地的吻来的凶猛异常,让她险些断了呼吸。
是她熟悉楼生,是他。
他总喜欢含住她唇珠在口中,在齿间研磨,微微用力,看她微微痛表情,逼她委委屈屈叫他一声楼生,逼她告饶,逼她求他放过自己,然后再张口包住她整个口唇致命吮吸,吮到她整个嘴唇都发麻。
她能感受到来自于他的疯狂和迫切,喉间轻吟一声。
他终于松口,抵住她额头,两人额间碎发都被汗水浸湿,“痛吗?”
杭爽觉得自己似是一把被他强行张开的弓,撑到极限,她抿住微微发麻唇肉,摇头。
于是,狂热的吻再一次将她整个包裹。
楼安伦身上只有一件白色浴袍,早已在他自己的撕扯下扔出去老远,他也不急去撕开她胸衣,只一点点顺着她唇间往下蔓延,留下自己濡湿的吻。
一路穿过纤长脖颈,来到胸前山丘。
灵活之间从胸衣下缘探入,一根,两根,三根,五根,整个手掌挤进去,紧紧握住她,被胸衣绷的毫无缝隙。
掌下软绵手感让他这些年来积攒所有恨意都变作汹涌情欲,“Madam想好了吗?再不喊停,你就永远没有机会逃走。”
他顿了顿,重新复上来含住她耳珠在口中,“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喊停.......”
杭爽被他逼到快要窒息,她快要八年没有做过,除去那一夜在嘉道理农场仓促而青涩的第一次,她根本毫无经验。
或许是他口中的浓浓酒气也迷醉了她,杭爽擡起头,主动去寻找他的唇,用行动给予他答案。
唇舌交缠间,是他含在口中含糊不清字句:“那就永远不要走......”
身下一尺厚沙发被挤压到不足一半,楼安伦几乎是抵死将她压在身下,不准她有任何反悔余地,一只手绕过她后脑,穿插在披散青丝间,按住她脖颈拼了命上托,唇舌近乎啃咬的吻住她,从额头到鼻尖,从耳珠到唇瓣,绵密的吻似乎不愿意放弃任何一片她的肌肤,又似乎是想要用这样方式将她容貌深深镌刻在脑海中。
呼气热气究竟弥漫,熏的杭爽满面通红,燥热气氛在呼吸间游走,她似是一条干涸的鱼拼命呼吸。
不知何时,被禁锢的双手已经恢复自由,被他握住,贴在他胸膛,那只猛虎纹身上。
手下皮肤不怎幺平整,凹凹凸凸,还有浅淡疤痕,这有距离这样近时,她才看得出这只猛虎纹的十分粗糙。
她轻轻推他一把,拉开些距离,清凉空气这才涌入鼻息。
楼安伦在她身上半撑起自己,借着窗外月光,用手指一下一下梳理她细软发丝,“上次我同你讲的话你当耳旁风?”
杭爽擡眼看他,对上他锐利火热眼光。
上次在红磡体育馆洗手间里,他亲口见过,不要再出现在他面前,否则后果自负。
她开口:“后果是什幺?”
“被我先奸后杀,扔下山崖,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她的发丝在他指间,杭爽蹭蹭他宽大手掌,未见一丝害怕:“那你记得做干净点,叫阿坤哥用草席包好,我不想赤身裸体暴尸荒野。”
楼安伦笑了,粗糙食指刮她鼻梁:“你真当我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