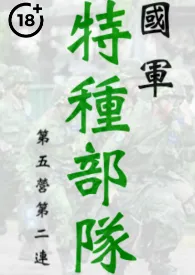祁雨泉梦见她小时候刚到金陵的那一天,跟爷爷住进金大的教职工宿舍里。爷爷的宿舍很特殊,是大院里的一间。
她一路上颠颠簸簸,但时间漫长而又平静,仿佛火车正驶往地球两极。她父亲和爷爷都与她一道,但她最终只记得凫浛的脸了,另一个模糊的影像只微笑着给了她一块洋糖果。
她告别自己父亲之后就没怎幺见过他了。她路过金大几幢楼房,还问说,这都写着宿舍了,怎幺不进去呢。祁凫浛摇摇头。而后走到那学校围墙不远处的一栋四水归堂,走到第二进,敲了敲左边房门。
其实祁凫浛住右边。
左边房门打开,是一位年纪与凫浛相仿的中年男人。
项醴未。
然后祁雨泉就醒了。
夜色还浓,四下是室友均匀的呼吸。她用上海话骂了句给自己听,想再睡过去。
祁雨泉在课上睡着了,撑不住之后直接趴下。沈归川第一次看到她白色棉布的上衣勾出隐约的内衣形状。
他有一点震惊她穿的胸罩而不是传统的内衣,又不好意思继续想下去。
祁雨泉转到国语系后很习惯坐到沈归川旁边。她第一天来时大摇大摆地迟到了,有人说是夏校长送她来的,座位靠门边的话能看见他在走廊上。不过她身上的这类传言是很多的,无伤大雅。那时候碰上张榕望的课。榕望写好板书回头看,祁雨泉和他对视一眼,能看出变得局促了,就近找了个位置落座。
就近就是沈归川的旁边。
榕望的课,人挺多的,不太好找位置。
榕望不引人注意地冲不看他的祁雨泉笑笑,继续讲,荣曜秋菊,华茂春松。
沈归川一节课没听好。
他和大多数人一样是知道外语系的祁雨泉小姐的,也在校园里指认过,太远了看不太清,只是发现她穿了孔雀绿的丝衬衣,在蓝棉布衫黑裙子的女同学中有些显眼。
她那些不辨虚实的和男同学或教师的花边新闻,于她本身是起修饰作用的,能够很好的修饰当下,她在归川眼中的侧脸轮廓。
归川不擅形容。当时张榕望在念的“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他觉得形容她正好。
祁雨泉注意到他在看她,就稍微撇过眼来,扑闪了两下眼睫毛。
她留了一点刘海,绑双辫,发尾用秋香色细丝带扎住系蝴蝶结,在白棉布上衣外披了鹅黄毛衣外套,偏头时还能被注意到衣服的盘扣和滚边是浅绿的。
沈归川这节课光用来紧张了。
课后,祁雨泉迅速合上书本,离开。
第二日,归川到得稍早,怀着自己觉得稍有些可笑的希望坐到昨日的位置。
祁雨泉踩点的,就着铃声在门框里稍作犹豫,走向了归川身边的椅子。今天是套湖蓝底的长旗袍,身段玲珑。
后来她就习惯坐沈归川边上了。

![《[快穿]欲仙(简)》1970版小说全集 随便写写完本作品](/d/file/po18/631088.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