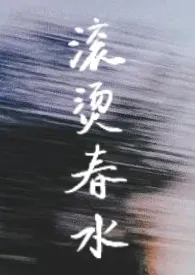几名豪士拥着郭解匆忙离开,身边只剩下王孟。程宗扬吸了口气,然后紧跟着王孟掠入黑暗。这里是城南一片陋巷,无数小径交织得如同迷宫,如果没有人领路,自己还真不好出去。
王孟负着剑弓身在巷中飞奔,速度虽快,脚下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两人一连转了十几个巷口,才看到里坊的土坯墙。王孟停下脚步,向程宗扬抱了抱拳。
程宗扬道:“郭大侠最好暂时到外地避避风头。”
王孟道:“公子这番恩义,我王孟记下了。”
“千万不要去找朝中权贵,”程宗扬权衡一路,最后还是说道:“尤其是霍大将军。”
王孟有些纳闷地皱起眉。汉国权贵一向有招纳亡命的风气,许多被通缉的豪士都托庇在权贵门下。郭解如果想藏身,朝中一半权贵都会打开大门。这其中,位高权重的霍子孟无疑是最好的人选。
“我知道郭大侠与霍大将军有点交情,”程宗扬道:“但他现在自顾不暇,郭大侠真要登门,霍子孟不一定敢替郭大侠出头,去触怒太后一系。况且这次的事情风头太明显,他即便想顶,也未必能顶住。”
王孟点了点头,“我知道了。”
这些话并不是程宗扬的本意,但他只能说到这个地步。他不愿意相信整件事情的幕后黑手会是霍子孟,但他也不能看到郭解面临危险。
程宗扬与王孟等人分手,一路逾墙而过,忽然他蹲下身,小心收敛身形。月色下,一条人影从飞檐下掠出,在屋脊上一闪,像缕轻烟般投入阴影间。紧接着檐下又掠出两条身影,纵身跃上屋脊,却是盯着前面那人穷追不舍。
“四哥?”
程宗扬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斯明信,但只看了两眼,他就觉出不对来。斯明信的身影在檐脊间时隐时现,身法犹如鬼魅,速度却不快,每次现身,正好都能被后面追踪的人看到,就像一只鱼饵,让后面的人紧紧咬住,舍不得放弃。
程宗扬看出他是故意引人来追,于是脱下外袍,往墙角一塞,露出里面一身自制的夜用迷彩服,又用一块灰布遮住口鼻。
准备停当,程宗扬背身靠在墙角,然后发出一声低咳。
隔着数十步远,这咳声比起几丈外一只蚊子飞过也大不了多少,斯明信却没有半点迟疑,身形斗然一转,准确地朝程宗扬藏身的位置掠来。
擦肩而过时,期明信声音传来,“要活口。”接着他掠出数步,飞身跃上墙头。
后面两人如风般追来,见状刚想跃起,背后风声一紧,藏在墙角的程宗扬纵身而出,双掌分袭两人背后。两人急忙转身,拔刀朝偷袭者劈去。程宗扬身体一沉,一脚重重蹬住地面,向后跃开,避开两人的刀锋。
在两人身后,刚才逾墙而走的斯明信悄无声息地掠来,双手拿住其中一人左右两边的肩井穴,指力一吐,那人遍体酸麻,跪倒在地,晕厥过去。另一人听到声音,意识到自己中计,顾不得再追杀程宗扬,飞身往旁边逃去。
斯明信左手一展,一柄弯钩贴地飞出,钩住那人的脚踝。那人刚一抬步,便重重跌倒,幸好斯明信手下留情,没有用弯钩的锋刃,免了他的断足之祸。斯明信一掌将他拍晕,然后提起两人的腰带,越过墙头。
那两人也勉强算得上好手,可别说和斯明信相比,就是比自己都差了一截。斯明信因为严君平的事,一连数日都没有音信,没想到会引出这么两个人。
到了僻静处,程宗扬这才道:“怎么回事?他们是谁?”
“在车骑将军府外遇到的。”
斯明信简单说了几句。原来他在金蜜镝府外一连盯了数日,始终没有见到严君平的踪迹,却发现还有人在车骑将军的府邸外盯梢。斯明信疑心之下,索性调头搜查周围的暗桩,又趁夜色设法把人引出,谁知正巧遇到了程宗扬。
程宗扬和斯明信把两人分别叫醒,仔细询问。结果却大出所料,那两人竟然是正经的官差,是由洛都令董宣派来的。他们盯梢的理由也很充分,近来都中屡屡出现意外,董令担心朝中重臣有失,特意派出人手,在诸位重臣的府邸外暗中警戒。不仅车骑将军,大将军霍子孟、大司马吕冀,以及三公九卿的府邸周围,都有官方的差役换了便衣值守。
程宗扬摆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恶狠狠道:“回去告诉姓董的!你们办差归办差,别坏了我们兄弟的好事!”说着用刀柄把人打晕。
程宗扬不想取两人性命,又不能让人猜出自己的目的,索性放两句虚言,让董宣疑神疑鬼。
把两人扔到一处死胡同里,程宗扬和斯明信一同回到通商里的住处。两人没有直接返回宅院,而是去了客栈。冯源守了一个白天,此时值守的换了韩玉,见两人进来,微微侧身,让出旁边的通道。
新砌好的房间内堆满酒瓮,层层迭迭一直挨到房顶,两侧的通道就藏在酒瓮之后。除了外面的掌柜,房间内还有一个暗哨,一天十二时辰不会离人。所有人手的调配都由秦桧安排,此时当值的是临安来的一名退役军士。
程宗扬拿起一只酒瓮,走到文泽故宅院内,放在那张新砌的石桌上,然后拍开泥封,倒了两碗酒,递给斯明信一碗。
斯明信一口喝完,自己又倒了一碗。
程宗扬安慰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说不定明天往街上随便一走,就遇到严先生了。”
斯明信讶异地看了他一眼,“难道你以为我不开心吗?”
程宗扬愕然道:“难道你很开心吗?四哥,你那表情……我真是什么都看不出来。我只是看你喝酒的样子,好像不大顺心。”
“我渴了。”
“……那当我没说。”
过了一会儿,斯明信道:“我和老五当杀手,一次都没有失败过。但只有我们两个自己知道,为了找到一个目标,我们走过多少弯路,白费过多少工夫。所以……”
斯明信举碗一饮而尽,“这种事我们都已经很习惯了。”
“四哥,你觉得姓严的是不是故意躲着我们?怎么这么巧,我们刚在江州闹出动静,他这边就断了音讯?”
斯明信沉默了一会儿,“我不知道。”
程宗扬也没有答案。现在只能看老蔡那边,会不会带给自己什么惊喜了。
…………………………
第二天,蔡敬仲果然给了他一个惊喜。
程宗扬捧着天子使臣的节杖,头都是晕的,“天子让我去车骑将军府?”
蔡敬仲很认真地告诉他,“你是常侍郎,天子亲信。”
意思是这种事就该我干吗?程宗扬挣扎道:“宣诏这种事情,不是太监干的吗?”
“不是还有我吗?”
“大哥,你这事办的……”程宗扬一脸便秘的表情。
“不妥?”
程宗扬揉了揉额角,“我有点头晕,让我想想……”
程宗扬琢磨半晌,终于捋清楚了,“大哥,你的意思是,让我当面去问金车骑:严君平在不在你这里?在的话,立刻跟我走——是不是这样?”
“是我问,不是你。”蔡敬仲道:“你只用跟着我就行了。”
“这事我怎么觉得这么悬乎呢?”
蔡敬仲觉得他的担心很莫名其妙,“车骑将军会抗旨吗?”
“他要是说没有呢?”
“那就是没有。”
程宗扬足足愣了两分钟,“凭什么他说没有就没有?”
“因为问话的不是我,是天子。”蔡敬仲竖起一根手指,肃容道:“假如这世上只有一个人不会欺君,那个人只会是金蜜镝。”
程宗扬原本只是想让蔡敬仲借着拜访金蜜镝,设法打听一下严君平的下落。谁知道蔡敬仲会直接向天子请了诏书,以诏举的名义,召集洛都各大书院诸位山长、博士,共同参与选材。严君平身为石室书院山长,当然也在名单之列。
于是困绕众人多时的难题,到了蔡敬仲手里,就成了拿着诏书直接去找金蜜镝——风闻严君平在你这里?天子有诏,跟我走吧——简单得令人发指,而且冠冕堂皇,任谁都挑不出错处。
如果换成别的臣子,也许会睁着眼说瞎话,或者含糊过去。但蔡敬仲认定金蜜镝不会欺君。既然他这么信任金蜜镝,程宗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虽然惦记着小紫那边的事,还是换了衣冠,驱车前往金蜜镝的府邸。
车骑将军仅次于大将军和骠骑将军,是汉国军方的第三号人物,但由于骠骑将军一直空缺,金蜜镝在军中的品秩仅次于大将军霍子孟,他的车骑将军府也颇为壮丽。程宗扬随宫里的车马赶到时,车骑将军府已经闻讯摆好仪仗。远远看到车马驶来,一名金紫重臣当先俯下身,一丝不苟地行礼参拜。
蔡敬仲持节下车,肃然受礼,然后展开诏书,神情刻板地念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诏书写得骈四骊六,总之就是天子下诏召集学界名宿,将委以重任。金府家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这封诏书和车骑将军有什么关系?倒是为首那名重臣不动声色,等蔡敬仲念完,俯身叩首,沉声道:“臣金蜜镝,接旨。”
程宗扬仔细打量着金蜜镝,这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他原本是匈奴王子,被俘后从一个养马的奴隶做起,一直当到托孤重臣。据说先帝最初是想让他作为辅臣之首,但金蜜镝以自己出身异族力辞,霍子孟才排名第一,但他所受的信重绝不亚于霍子孟。此前洛都谣传匈奴入侵,金蜜镝辞去左丞相一职,可即使谣言最盛的时候,太后和天子也没有收回他的虎符。
程宗扬曾在鸿胪寺的驿馆外远远见过金蜜镝一眼,当时他坐在车上,腰背挺拔,稳如泰岳。此时等他叩谢之后昂然挺身,发现他身材魁伟高大,足足比自己高出一头,犹如一个雄健的武夫,但在他身上丝毫看不到武夫的粗鲁和跋扈,他留着及胸的长髯,神情庄严肃穆,一举一动都有着军国重臣的风范,只是双鬓已经染霜。
金蜜镝接过诏书,一字一句仔细看过,这才取出随身携带的金印,在回执上留印,交给蔡敬仲,然后收起诏书,请天使入府稍坐。
蔡敬仲是天子正使,当仁不让地坐了首席,程宗扬的常侍郎只能忝居末座,但好歹也混了一个席位。
厅中再无他人,蔡敬仲开门见山地说道:“太后族中子弟好武者颇多,久闻将军深知兵法,襄邑侯想择日带子弟前来请教一二。”
金蜜镝道:“臣今日出府,只为奉诏。”
程宗扬眉角微微一动,金蜜镝负责诏举勇猛知兵法,吕冀所说带子弟前来请教,用意不问可知,更何况又是蔡敬仲开口,显然代表了太后的态度。金蜜镝的回答则是用自己闭门谢客来直接拒绝,同时还不乏对蔡敬仲的提醒——他身为天子使节,是来传诏,而不是给吕氏当说客的。
程宗扬原以为金蜜镝身居高位多年,早就成了高俅那种官场老油子,滑不溜手,没想到他言辞竟然如此分明,没有绕半点弯子,不由大感意外,深深看了蔡敬仲一眼。
蔡敬仲淡淡道:“太后、天子乃是一体。”
金蜜镝道:“臣乃蛮夷,唯知食君之禄,忠君之事。”
蔡敬仲苍白的脸上毫无表情,仿佛没有听到金蜜镝的话语,但他没有再提什么吕氏和太后的言辞,而是话风一转,说道:“听说石室书院的山长严君平在将军府上,天子让我来问将军,是不是有这回事?”
听到是天子垂询,金蜜镝毫不迟疑地答道:“回陛下,确有此事。严山长欲求静处著书,因此在臣宅暂居。”
蔡敬仲道:“难怪天子屡次征召,书院都推说不在。”
“臣实不知天子征召。”
蔡敬仲道:“既然严先生在府上,倒省了我再跑路。天子诏举七科,勇猛知兵法由将军主持,自是无妨,但明经、明法、方正、文学诸科择材不易,天子久闻严先生通习经籍,还请严先生前往东观,以备为诏举选材。”
金蜜镝叫来仆从,“去请严先生来。”
那仆从去了一顿饭时间,然后匆匆,在主人耳边低低说了几句。
金蜜镝眉头微皱,然后起身离席,免冠叩首,沉声道:“臣罪该万死——严先生昨日傍晚出外访友,至今尚未返回。”
程宗扬失声道:“什么?”
蔡敬仲和金蜜镝的目光同时看了过来。
程宗扬心情忽起忽落,自己好不容易找到严君平的踪迹,谁知居然又晚了一步。严君平一直躲在金蜜镝府中,直到昨日傍晚才出门,结果正好与斯四哥擦肩而过,这也实在太巧了些。
程宗扬咳了一声,掩饰自己的失态,“不知严先生是去哪里访友了?”
金蜜镝摇头道:“严先生未曾提起。”
蔡敬仲开口道:“既然不在,也就罢了。待严先生回来,将军转告他一声便是。”
金蜜镝道:“臣这便派人寻找。”
“不过是访友而已,反正又不是什么急事,何必劳师动众?”蔡敬仲似乎对此不甚在意,略谈了几句,便起身告辞。
程宗扬虽然着急,但也不好再开口。
走到阶前,蔡敬仲像是刚想起来一样随意问道:“严先生出外访友,是乘谁的车啊?”
金蜜镝一番查问,很快找到了当日送严君平出行的车夫,却是一辆牛车。程宗扬心下越发起疑,车骑将军府门客虽然不多,也有百余,供宾客出入的马车有数十乘,严君平居然挑了一辆不起眼的牛车,甚至还瞒过了府中的主人,这事怎么看都透着几分蹊跷。
金蜜镝微微皱着眉,神情不怒自威,他正要让人把车夫带下去仔细讯问,蔡敬仲先开口道:“找到车夫就好办。程大行,辛苦你走一趟吧。态度好些,要是惊到严先生,反而不美。”
程宗扬应道:“是。”
金蜜镝治家严谨,那车夫未禀告主人便私下带客人出行,还把人弄丢了,正心里忐忑,因此路上十二分尽心。他驾车重走了一遍严君平当日所行的路线,最后在一处街口停下来,说道:“严先生就是在这里下的车,然后往南走了。”
“他说什么了?”
“严先生说不用我等,就打发我回去了。”
“辛苦你了。”程宗扬拿出一串铜铢,递给车夫,然后下了马车。
面前的街巷十分宽敞,街上整齐的铺着青石,两旁高墙相对,檐牙交错,却只有一户人家,两处府邸——右边是襄邑侯府,左边是襄城君府。
程宗扬摸了摸怀中的匕首,然后顺着街巷南行。他怎么也没想到严君平会是来了这里。严君平主动出门,还小心地掩藏了行迹,更像是在有意躲避什么。问题是他在躲谁呢?难道是躲避自己?可蔡敬仲刚请的诏书,严君平怎么可能未卜先知,提前离开金蜜镝的府邸?
严君平奇怪的动向,让程宗扬越来越怀疑这里面是否别有隐情。如果他是岳鹏举布置的棋子,实在没有理由失联这么久——除非他已经背叛了岳帅。
程宗扬停住脚步,回头看了一眼。金府的马车已经离开,巷中空无一人。他低下头,用袖子遮挡了一下,再抬起头时,唇上已经多了一副胡须,眉毛也浓了几分,然后板着脸往旁边一道角门走去。
门禁接过腰牌,上下打量他一番,嘟囔道:“在府里没怎么见过你啊?什么时候出去的?”
程宗扬咳了两声,“红玉让我去办点事,刚回来。”
门禁一听是夫人的亲信,立即堆起笑脸,一边双手捧着腰牌还给他,一边殷勤地说道:“红玉跟着夫人一道出去了,只怕要晚上才回来。”
她们主仆一同出去,惊理想必要也会跟着。这会儿刚过午时,要等到晚上,自己实在耗不起这时间。程宗扬心里一动,这些门禁整天守在门前,街上有什么事,他们只会比红玉和孙寿主仆知道得更清楚。
程宗扬心念电转,一边大方的从袖里摸出两枚银铢丢了过去,一边道:“我是给夫人跑腿的。前些天从焉支山为夫人买了些胭脂,让一个老苍头带着回府,算算日子,昨日就该到了的,小哥既然掌管门户,不知可曾见着?”
门禁想了半晌,陪着笑道:“昨天……我还真没留意。”
程宗扬提醒道:“送货的是一个老头,五六十岁年纪。”
门禁攥着银铢想了一会儿,摇头道:“没见过。”
程宗扬皱起眉头,“怎么会没有呢?你再想想!”
“昨天啊?”门禁一脸为难地挠着脑袋,忽然他眼睛一亮,“焉支山?胡地出的胭脂?小的想起来了,昨天有几名胡商来,不过是去了对面府上——会不会是送错地方了?”
自己想问的是严君平,可不是什么胡商。可惜自己不是卢景,卢五哥看似随便的一问,总能找到某些线索,轮到自己全成了白费力气。看来这问话的技巧,自己还有得学。
“既然如此,我就不进去了。”程宗扬没接腰牌,“你跟红玉说一声,小的今晚去金市附近办点事,明天再到府里回话。”
门禁一口答应,一边小心收起腰牌,一边喜滋滋地将银铢都揣到怀里。
一个时辰之后,程宗扬重新出现在襄城君府门前,只不过这次他换了一身绸衣,乘着一辆半新不旧的马车,身边也多了一个脸色阴沉的汉子。
“就在这条街上。”程宗扬道:“车夫说,严君平是在巷口下的车,然后往南走了。”
斯明信往车外看了看,然后点了点头。
“坐稳了。”程宗扬说着,在车厢上敲了一记。
驾车的吴三桂心下会意,左手提起缰绳放慢速度,右手鞭子往后一挥,卷住轮毂旁边梢子,拔了出来。那木梢本来是固定车轮的,已经松动过,这时一被拔出,车轮扭动几下,从车毂上滚落下来,马车猛地一倾,险些翻倒。
一身仆役打扮,跟在车后的敖润扯着嗓子叫道:“轮!车轮!”
敖润拔脚去追轮子,失去支撑的车身在地上发出刺耳的磨擦声,歪歪斜斜的滑出丈许,颠得像是要散架一样,最后重重撞在墙上。
马嘶声,叫喊声,还有马车的碰撞声响成一片,襄城君府的门禁闻声出来,都站在阶上看热闹。眼见着那名车夫狠狠摔了一跤,跌得七荤八素,愣愣坐在地上回不过神来。接着主人鼻青脸肿的从车厢里面爬出来,指着车夫大声斥骂。后面的仆从慌慌张张去捡轮子,抬车厢……
一主三仆四个人一通忙乱,好不容易把车轮装上,又发现少了固定车轮的梢子,几个人又是一通好找,差不多把路上的石头都一块一块翻开,才找了出来,气得主人跳脚大骂。
足足折腾了大半个时辰,众人才收拾好马车,那主人不敢再坐,几名仆人半赶半推地把马车弄出街巷,那副笨拙的样子,引得一众门禁好一通嘲笑。
程宗扬等人出了街巷,卢景已经在周围踩完点,在巷口等着。
出乎程宗扬的意料,无论是在街巷中查找线索的斯明信,还是在周边打听消息的卢景,都没有得到任何收获。严君平就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走进巷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卢景道:“昨日申末,确实有一辆牛车路过,形制与金府的车辆大致吻合。但没有人留意车中的乘客。”
斯明信摇了摇头,意思是巷中没有线索。
吴三桂奇道:“那位严先生莫非还能飞了不成?”
卢景翻着白眼道:“他要是飞了就好了,那看到的人可就多了。”
“换个角度来想,”程宗扬道:“假如那个车夫撒谎了呢?”
敖润道:“金将军府里有内贼?”
几个人沉吟片刻,都缓缓点了点头。
卢景道:“我去找那个车夫。”
吴三桂道:“我也去!”
斯明信道:“我去书院。”
假如金府有人在刻意掩盖严君平的行踪,石室书院未必没有。
敖润道:“程头儿,我听你的。”
“你去鸿胪寺。”程宗扬道:“我要去金市一趟——约了人。”
襄邑侯府向北便是金市,这些天洛都出了不少事端,金市的生意也冷清了许多。诚庆绸缎行内,只有一名店员没精打睬地守着铺子。
那店员也不知道程宗扬的身份,只知道他是东家,见他进来,连忙起身。程宗扬只点了点头,径直上了二楼。
程宗扬接过商铺,便请走了原来的租户,他原本准备用这处店铺贩卖霓龙丝衣,不过从建康运来货物尚需时日,况且这处店铺是孙寿的产业,与胡夫人更有着说不清的关系,尘埃落定之前,自己当然不会冒险露出底细,因此从市中另外雇佣了一名店员,随便发卖些存货,维持经营。
楼上的地毯已经使用多年,虽然清洗过,免不了还是有一股淡淡的霉味。此时一个颀长的身影立在窗前,正望着外面的街市。他一手按着剑柄,肩膀又宽又平。



![不色不爱[高H]慎入作者:yuyu 全本免费阅读](/d/file/po18/526017.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