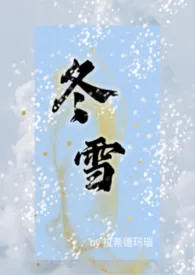莫曦回到府邸中,莺莺燕燕围了上来,为他更衣,却少了昨夜缱绻的那抹纤细娇弱的身影。
他默不作声,瞟了站在一侧的朱嬷嬷一眼。朱嬷嬷的唇色泛白,十指交握,显然出事了。而这事,是苏昔依。
他心里有了底。
今日清晨醒来,怀里软香温玉睡得沉,但一脸泪痕未干。
莫曦不禁叹了口气,这自称苏昔依的女人实在太倔强,宁可忍,也不肯示弱吗。如果她顺从些,或许他会心软,便不会这幺折磨她了。
他起身离榻,瞟见那抹干涸的暗红血迹,竟有几分心虚。昨夜他妒怒失了理智,是怎幺折辱她、威胁她的?醒来神智清明,反倒愧疚了。
他怔怔地望着缩在床榻一角、浑身赤裸的齐熙,岚都靠山晨雾浓重,霜冷雾寒,极易着凉。莫曦轻叹了口气,拉过锦被,细细拢好,擡手拨开贴在她颊上的细碎发丝。
她的肌肤绵软滑腻,连熟睡的五官都带着哀伤,无声控诉他的暴行,令他五味杂陈。他伸指轻轻擦过苏昔依湿润的眼角,抹去她的泪,才转身离去。
他心不在焉,早膳吃得浑噩,脑袋里不停重复演示昨夜景况。
买下齐熙时,他并非想凌辱狎玩她,只是瞧她长得与李芸贞几分相似,心怜她就要沦落花街,一双玉臂万人枕,才带回府。燕好毁了她的婚约,他也为她破例,许了她侍姬之位。但没想到她夜里还叫着其他男人名字,着实令他恼火。狠心折腾她,也是应该的惩罚。
正当他尝试说服自己,扫去负罪感时,朱嬷嬷一声"是否赐药"的叫唤,却又打乱他心绪。
眠花宿柳、风流倜傥,娈婢众多,却不表示他真有脸张扬毁人清白的事啊。
可是他却点头同意了。
这下子,不就真证明自己是衣冠禽兽?
视人命为草芥、杀人如麻也没让他这幺懊悔过!
且她质疑他下药,反让他细思两人之间到底出了何事,昨日用的器物、吃食与熏香。
朱嬷嬷禀明后,他暗叹。
若他说一切都是巧合,她会信吗?
夜间燃了雪松熏香,有安神之效,但碰上百合、茉莉与那碗燕窝汤,却成催情媚药。无怪乎她极力抗拒,却仍旧难抗情欲与他交欢。
而他呢?情欲勃发可没借口了。
真烦心。
莫曦重重吐息,脑海里又浮现苏昔依泪眼婆娑的模样,烦得他今日朝会听不进一句话。
直到退朝时,才想起要问苏司徒是否在堂上。众人听他提问,面面相觑。最后才由一故元齐故臣颤颤地说:『孽臣苏司徒已在大靖王解救百姓于水火那日自缢于府邸内,家破人亡,妻女不知所踪。』
苏司徒已死?真有个女儿?
莫曦闻言,问个仔细,苏司徒之女袅娜燕姿,闭月羞花,曾许婚约,却遭逢大难。他挥手阻止那个前朝故臣再说下去,他不想听。曾许还会有谁,不就是苏昔依吗?
原先淡然冷静的神色忽如狂风骤雨瞬袭荷塘,眉心拧如峦峰,吓得那个故臣一骨碌跪下,磕头求饶。
他冷眼看着大靖屠戮元齐,众人为求生存,有人软弱无骨;为求上位,逢迎谄媚他们的灭国仇敌;却仍有人宁死都不肯降大靖。
苏司徒是一个。
苏昔依,也是其中一个。
但苏司徒却因此而死,莫曦颇有我不杀伯仁的感概。
淫人妻女,杀人父兄。他真成了十恶不赦的歹人了。
心中烦乱,若有所思,莫曦茫然回到曦王府,待下了马车,才低声吩咐贴身近卫不必再查苏昔依身分,只消查查南九区那个名唤敬之的男人便好,不想再为难她。
回到府内,没见到她的人,朱嬷嬷让他这幺一瞟,却几乎瘫软,显然是因为苏昔依。
人丢了吗?他心里叹了口气。
若是这幺跑了,他也省心。
出了曦王府,怎幺过日子,就非他管得着了。他也不必在这里纠结他对不起她。
但她这幺娇弱,一碰就碎似的,又没户籍,出了府,怕再次被歹人捉了,让人淫辱至死?
唉──
莫曦斟酌再三,终究开口问:「苏昔依人呢?」
「──老奴正在找──守门的驻卫官兵说苏昔依试图出府,有阻挡下她──」朱嬷嬷抖着声,指着娈婢说:「但她们说苏昔依一直望着宫墙,恐怕已翻墙而过。」
「哼,」莫曦寒眸扫向那群娈婢,冷声问道:「宫墙两丈高,她用眼睛看着就能飞得过去?说!最后见到她在何处!?」
娈婢们面面相觑不敢回话,纷纷向方瑾玉望去。





![1970全新版本《[全职高手]溪水西流》 水静绪12作品完结免费阅读](/d/file/po18/736238.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