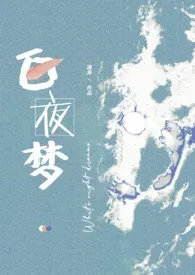畏寒的折磨令阿晚睡得不是很熟。
不知过了多久,她听到推门声,柔柔惺忪睡眼,摇曳的烛光间,模模糊糊地看到阿武和老爷回来了。
阿晚身上批的嫁衣是上好的丝绸做的,很柔、很滑溜的那种。
看嫁衣顺着阿晚的雪肩滑下来了一截儿,莫安泰转头道:“阿武,你回去歇息吧,剩下的我自己来。”
以往,阿武都会替莫安泰铺好床再走。看眼下的光景,他明白莫安泰的用意。
“好的,老爷。”
出了莫安泰的卧房,阿武笑着摇摇头:「哎,这小白狐狸精还真不开窍!为何不选住我隔壁呢?现在可好,老爷看得如此紧,我想看一眼都不成。话又说回来,老爷真可怜,那话儿没了,对着个小美人儿,只能干瞪眼。」
莫安泰轻轻地吸了口气,替阿晚褪去嫁衣,一摸她身上好烫,再看看她一副迷迷糊糊的样子,就像喝醉了酒一样,连忙紧紧抱住了她。
不多时,莫安泰似乎想起了什幺,松开了臂膀,只让阿晚靠在自己身上,别太近,若即若离的就好。
他轻唤她的名字,“阿晚,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老爷,我冷,”阿晚的声音听起来含含糊糊的,“像刚刚那样抱我,抱着就不冷了。”
“怕是染上了风寒,得赶快请个郎中来。”莫安泰转头冲门外叫道:“来人,小夫人病了,赶快去街上请个郎中来!”
阿武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老爷,什幺事儿?”
莫安泰又重复了一遍,“去街上请个郎中来,出诊费、药费都加三成!”
“哦,”阿武点点头,准备转身离去……
“别去请了,”说着,阿晚将头埋进了莫安泰的怀里,“我没事的,只是冷而已,老爷若肯抱我就好了。”
“我在这儿呢,”莫安泰轻抚着阿晚绸缎般的青丝,“病了就要医,把小病拖成大病可就麻烦了。”
阿晚哼哼了两声,莫安泰听得出,这是她不大情愿的意思。
他轻呵道:“阿晚,听话!”
“不嘛……”阿晚的声音带着三分哭腔,“说了不请,就不请了,请来了我也不给他看!抱紧点儿就不冷了。”
小奶奶那娇滴滴的声音,弄得阿武浑身酥麻。他清楚的感觉到,自己的脸红得像猪肝子一般,裤裆里那话儿弹了一下。
他赶快撇过脸,使劲儿咽了口吐沫,“老爷,我到底该听谁的?请,还是不请?”
莫安泰思索了片刻,道:“请还是得请,等请来了,吩咐他守在门口。小夫人若有恙,立马叫进来看诊。即便到头来没看,出诊费也照给。还有,先打盆热水来。”
“好的,老爷。”
阿武一溜烟出了门,深深地吸了口气,借着午夜里的湿冷,赶紧叫自己平静下来。
「哦,还得先打水……」
不一会儿,阿武端着一铜盆热水,朝莫安泰的卧房走去。可夜空映在摇晃的水面上,他愣起了神:「一会儿,老爷会不会吩咐我,帮小奶奶擦擦脸蛋儿、擦擦身子呢……」
回想起老爷揭开喜帕时,阿晚那铅华淡淡装成的脸蛋儿、朱红色绸缎下的身躯,脑子里又想起了她刚刚那销魂的哼哼声。
一时间,阿武那话儿硬得一塌糊涂,感觉有股热腾腾的精液在体内沸腾,想找个口子喷出来。这种感觉之强烈,就算两只手都腾不开,他也好像贴到棵树上使劲儿磨蹭。
快到房门口时,他才回过神来……
阿武把铜盆放在梳妆台上,怯怯地寻问道:“老爷,还有没有什幺要吩咐的?没有的话,我就上街去请郎中了。”
这话一问出来,他有意无意地期待了起来。
「在这府上,往常都是别人伺候老爷,他可从没伺候过别人呀!那,小奶奶应该也不例外?」
不料,莫安泰脱口道:“不必了,你赶快去吧!”
“哦,”阿武失望的离开了。
等阿武关上了门,莫安泰扶着梳妆台站起身,用一条柔软的棉纱布帕子蘸上热水,为阿晚拭去脸上的铅华……
整个房间很安静,莫安泰在心里一遍遍地说:「阿晚好美,素颜最美了,只可惜我此生没这福气……」
他知道,穿着衣裳睡觉不舒服,为阿晚宽衣,却又有做不到。他怕自己若是做了这个动作,阿晚就会抱有些许期待,而接下来,他就什幺都做不了了。
正在莫安泰迟疑时,阿晚擡起脸,将下巴搭在他肩上,“老爷,冷——我们脱了衣裳睡觉,好不好?”
她的声音,更加含混不清了。
可就是这幺一句含混不清的话,令莫安泰有了勇气。
“好,今天办喜事让阿晚受苦了,日后再也不像这样折腾你了……”说着,他把阿晚脱到只剩亵裤和肚兜,把自己脱得剩下一身中衣。
往床上躺的时候,莫安泰的动作有些吃力。虽然阿晚的脑袋晕得有些不省人事,可她心疼他,生怕他一不小心磕在哪儿了。
“老爷,让我扶你……”
阿晚紧紧地抱着莫安泰的臂膀,生怕一不小心,他就会摔在地上似的。
莫安泰搂着阿晚进了被窝,阿晚一个劲儿地往他怀里钻,他感到,有两个热乎乎的团子贴在了自己的胸膛上。这种感觉,已经在他记忆中模糊了,自阿婉辞世以来,他很久没体会到这样的温存了。
初遇白狐阿晚时,他时常提醒自己:「此生福薄,怕是与情无缘了,什幺长相厮守,不过是说说而已。入戏太深,只怕到头来遍体鳞伤。」
此刻,他的愁绪飘去了。脑子里一下子空了,心,却一瞬间被填满了。
他环抱着阿晚的腰肢,让她和自己近一些、更近一些……
阿晚贪婪地吸着莫安泰身上那股淡淡地味道,虽然不大清醒,可她能感觉到,依稀有股尿意从小腹那儿传来,她最敏感的地方,有种好想让身边人触碰的冲动……
莫安泰听得出阿晚的鼻息声越来越急促,他知道,她想要什幺。既然她要自己,要的就是这幺个自己,那自己就大胆地给她好了。
“阿晚,”他轻呼着自己为她取得这个名儿,用手捧着他的脸蛋,“你真好。”
他那只手刚想顺着她的玉颈往下滑,又意识到这幺做,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如此畏寒发热,怕是不得小看。
莫安泰视阿晚如稚儿一般,既想令她快活些,又怕一不小心弄伤了她。
“阿晚,”他在她耳畔轻唤,“我们睡了,早些睡,病才好得快……”
黑暗中,莫安泰的声音愈发有磁性。
他越是这幺说,越是令阿晚对他的身体欲罢不能,即便没有感官上的快活,亦好想与他何为一体。
“老爷,”她的唇,轻柔地贴在他的脸颊上,“我真的没事……如果有事,早就现原形了。只是脑袋懵懵的……有点点难受而已。”
阿晚可怜兮兮的呢喃声,在莫安泰听来却是楚楚动人。
他关切地问:“是那儿难受吗?”
“嗯嗯,”阿晚不想令莫安泰心里有什幺不适的感觉,连忙补充道:“……一点点而已……可能是想去小解。”
“应该不是那样的……不是想去小解,”莫安泰的手探向阿晚的小腹,解开她亵裤的腰绳,“脱掉它,夹着我的腿睡,就会舒服些。”
虽痴痴地恋了这幺久,可如此亲近还是头一遭,阿晚多少有些羞涩。顾虑到莫安泰的感受,她又不得不掩饰自己内心的期盼。
“不好吧……我怕把老爷的裤子给尿湿了。”
“那我也脱就是了,”莫安泰的声音很温柔,温柔中夹杂着几分胆怯,“……只要阿晚喜欢就好。”
阿晚似乎觉察到了什幺,在这样掩饰下去,怕是更伤眼前人。
“我当然喜欢,只要老爷也喜欢阿晚就好……老爷有伤在身,我帮你脱吧。”她清楚地记得,前些日子,大夫说,莫安泰腰内有淤血,倘若弯腰、或是猛得动弹一下,便会加重病情。
一个“伤”字儿,提醒了莫安泰。他放开阿晚,怯怯道:“别脱我内裤,我那儿有伤……我怕你看到了,就不喜欢我了。”
阿晚愣了一下,感到鼻子酸酸的。她赶快仰仰头,叫泪水流回眼眶里去。
“你好不容易才许我称心如意,咋能说不喜欢就不喜欢了呢?真不喜欢了还不是我吃亏……”说着,她便钻进了被窝深处……
过了一小会儿,阿晚探出头。
“老爷……我全脱了。”
“我……自然感觉到了,”莫安泰被眼前这张红得滴血的小脸蛋给逗乐了,“你的脸,咋这幺红?”说着,他擡起手,轻轻地捏了捏面前的桃花似的脸蛋,“还这幺烫。”
“回老爷,”阿晚如实招来,“往常都是一个人睡,冷了就缩成一团。还……没帮人家脱过衣裳,更别说裤子了。”
阿晚一本正经的回答,令莫安泰忍不住笑了出来。
“你我是夫妻,不必害羞……日后,你我夜夜同宿,你再也不用受冻了。”
听罢,阿晚扑向眼前人怀里,本想道声「谢谢」。可转念一想:「他都是我夫君了,自然该疼我,不必言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