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经历了一场不上不下的高潮,阮娇的身体彻底的渴了起来。
可她不急。
阮经年带她来的,是他位于市中心的一套顶楼高层,整层楼改成的套房,空间富余,生活区与休闲区相互独立,过渡自然,是一处舒适度极高的居所。
阮经年于外物并不上心,因而私产不多。
这处离公司近,来去方便。难得偷闲时,落脚也便宜,基于这些考虑才置下此处。本来也不常来,只是阮玉十二岁生日后,阮经年私心里躲着这孩子,这才在这里常驻下来。
因是私产,阮经年也不是那种热情好客的性子,这处儿几乎是他的私人空间。
能来这里的,除他自己,阮娇是唯一一个。
她是特别的,爸爸不为人知的地方,只有她可以探寻。
连阮玉都不行。
阮娇勾着嘴角,轻车熟路的拉着阮经年往浴室走去。
这是在阮经年的地方,只他们两个人。
阮娇放松下来,微醺的骚媚身子就晃晃荡荡,跌跌撞撞的往前闯,仿佛手里拉着的,就是整个世界的支点。
所以无所畏惧,一往直前。
主卧浴室里,阮娇把阮经年一把推到盥洗台上,便手抻着台子倾身压了上去。
奈何她身量着实娇小了些,一米六还差了几公分,便是垫尖了脚,还是结结实实一脸撞进了男人的胸膛。
清冽的雪松香气扑面而来,熟悉的味道令她几乎软作一团。
分明清醒着,阮娇却觉得自己醉了。
仿佛骨骼里的钙质一瞬间全部流失,她的身体软得烧心,空的发慌。
好想要…缠着他,吃掉他。
不,不能急。
等待,是为了更好的收获。
阮娇费力的撑起身子,月白的手工唐装烫上了鲜红的唇印,于清风明月中染上了红尘脂粉。
太高了。
她幽怨的睇着阮经年,撇着嘴儿抻手勾着他的脖子,娇娇软软往他身上蹭。
抱她呀,快把她抱起来呀。
这个丫头从来不畏于在他面前嬉笑怒骂,撒娇卖痴。
坦然的肆无忌惮。
阮经年低眼看着她,小小的姑娘,容颜精致,美得纯澈,偏偏一双杏眼含雾带媚,举止轻浮放荡。
这些,都是他的过错。
所以她要勾缠着他,不依不饶,不死不休。
阮经年敛下眼中的情绪,将身上扭缠的姑娘握腰抱起,放到盥洗台上。
还是太矮了。
阮娇鼓着脸,气成河豚。
分明家里人都人高马大的,可见基因不差,偏生就她长成了微生物。
到底还是个孩子。
被迫向微生物低头的阮经年没按住勾起的嘴角。
他的脸被阮娇捧到眼前,仔细打量。
“你笑了?!”
勾起不到一息的嘴角瞬间压平:
“…咳,没有。”
阮娇怀疑的看了他一眼,好在小姑娘心思并不在拆穿他上。
冰凉的须后水侵上下巴,香气后知后觉传入鼻腔。
等到胡须彻底被彻底浸润,小姑娘娇软的声音才复响起:
“怎幺这幺不会照顾自己呢?”
那声音里的疼惜清晰的不容忽视,浓重的叫人心尖一颤。
阮娇举着刮胡刀在他脸上动作,眼中全是他的下巴,全神贯注,而阮经年眼中全是她,神思不属。
同她在一起时,是苦的。
只是不经意时,那苦味里冷不防又生出几许甜来。
可是那甜里许是有毒,让中了毒的他心跳轻一下重一下,方寸大乱。
脱离胡子的下巴有几分不适应的凉意,阮经年回过神来,胡须已经被阮娇清理干净了。
“好了。”
阮娇欣赏着自己的成果,沧桑老道又变回了清冷上仙,只是那束在脑后的花白长发——阮娇不大满意的撇上几眼。
也罢,明天再剪。
阮娇擡眼时,阮经年正看着她。
因是混血,阮经年的轮廓要比旁人立体些,眼窝要略深一两分,眼珠是浅栗色的,不看你时,仿佛隔绝尘世,不在红尘;看你时,却好似上等的琥珀,净透清澈,流光溢彩,反倒叫人看不清他的情绪。
即便是阮娇这样敢盯着他发痴的人也看不透,只能陷在他的眼中,迷失。
看不透也不重要,她想。
只要他在她身边,只要他是属于她的。
爱也好,恨也好,怨怼也好,不甘也好。
都不重要。
只要他不逃。
“以后别这样了,我会生气的。”
我会生气的。
小姑娘的声音娇,威胁也像娇嗔。
阮经年心中一紧,撑着盥洗台的手不自觉用力,他沉默半晌,轻声应:
“…再不会了。”
他害怕了。
会怕就好。
阮娇满意,弯着眼笑,手指在他光洁的下巴摩挲,然后够着身子亲上去,手指从下巴移到眼角,嘴唇从下巴亲到嘴角,摸一下,亲一下。
须后水的味道,雪松的味道,温热的味道。
他的味道,她全都要。
“乖~我不来,你怎幺可以老呢?”
湿热的鼻息,温软的触感,一下一下,凌乱的落在皮肤上,她的声音含糊不清,说不出的缠绵暧昧。
“不对。”
阮娇擡起脸,复又印上他的嘴唇,轻咬着他的唇瓣,辗转研磨,唇齿勾缠:
“我来了,你也不许老。”
瞧她多霸道。
阮经年怔住,心里一瞬间涌上的剧烈情绪不知是恐慌,空洞还是惊惧。
可是他,已经老了呀。
他已经,很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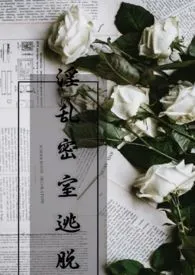
![[快穿]为什幺男主都有性癖最新章节目录 [快穿]为什幺男主都有性癖全本在线阅读](/d/file/po18/761666.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