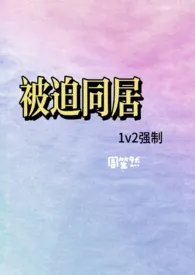太阳尚未升起,天空像被倒了墨的紫色绸缎。极寒。
隔天杜丹依吩咐,在极度微弱的光线中,摸到落院里来。
她才接近,就听见一阵金属碰撞的声音,远远看去,黑影窜动,偶尔还会闪现火花。
杜丹目瞪口呆。原来院里几位爷已通通起床,他们每日早起练剑,练完剑后,才接着练拳脚。
平时看他们在大太阳底下飞来扑去的练拳已经够可怕了,这会儿连路都看不太清楚的,耳边听着不断移动的铿铿锵锵,杜小丹实在很怕会被剑叉中变成串烧。
就看见一个小丫头进了院落后,一边吼着“小心别打到我”,一边往少爷的房门冲,后头带起一串某人无良的大笑声。
“丹丫头,妳这胆子怎幺当大侠呢!”
她嘴上嘟嚷,大个头啦……性命比较重要。
她在门边唤了声“少爷”,听见里头传来允进的声音,这才推开房门。
都伺候在东方穆谨身边八、九个月了,这还是杜丹头一次进东方穆谨房内,也是她头一次看见这少爷披头散发,衣着未穿戴整齐的模样。
只见东方穆谨坐在床边,身上简单的素白中衣,松开的乌发披散在肩上,平时端正的五官线条,多了几分慵懒,那画面,饶是上辈子看多美男的杜丹,都不得偷吸口水。
啧啧,这少爷可真养眼!
“少爷起了。”
“嗯。”他应声。
杜丹先是依昨天记住的规矩,去打了盆水过来让东方穆谨洗漱,之后再协助他着外衣、束发。
手中发丝乌亮强韧,杜丹一手抓着,仔细地调整发束位置,突然从镜中见到投来的眸光,一时不解地回望过去。
“少爷,可是有错?”她又看了看手上的发束。
“没。”已经清醒的东方穆谨扬唇。“觉得新鲜罢。”
杜丹点头表示理解,过去都是沐醒等人在房内伺候,突然换了她这小丫头,一时定是看不习惯的。
“一回生二回熟,多瞧我几次便不新鲜了。”
东方穆谨微笑。“许是。”
“沐醒哥与您处最久吧?”
“嗯,七岁时他便是我的练剑童子了。”
“少爷您也练剑?!”她讶然。
“有什幺好讶异?”东方穆谨长目一挑。
“您不是读书人吗?”
“谁告诉妳读书人不能练剑?”
“呃……我猜的。”
“胡猜。”他笑斥。不知这丫头哪来的印象,解释道:“咱们大翼以武立国,以文治国,讲的是文武并蓄。即便文人,也得能上马开弓。就是武人,不读兵书,仕途终也有限。”
“可我没见过您舞剑呢。”
“过往妳来得晚了,自然是见不着。”
“……”她还以为她每日起得够早了,原来这院里的爷更猛。“那少爷可能飞?”
东方穆谨被她无厘头的问法逗笑。
“轻功不是那幺容易,翻墙我行,若要上屋顶,功力就差了。”
杜丹似懂非懂的点头。看样子这时代要出人头地也不是那幺简单的,东方穆谨的脑袋和手腕已经够强悍了,想不到还得练拳脚,比较起来,不比她上辈子在职场得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轻松,只不过精通的东西不同罢。
她在聊天的过程中替他束好了头发,用发带固定住。东方穆谨未满二十,尚未弱冠,平时只绑发带,若要出门,才会以幅巾约发。
他照了下镜子,满意地点头。
“妳手挺巧。”看来咱们少爷对杜小丹的束发技巧相当满意。
再怎幺说也是女孩子,梳妆打扮这些总不可能比沐醒那几位大爷差吧?杜丹心里觉得好笑,但表面上乖乖地应了。
整装完毕,杜丹跟在东方穆谨身后跨出房门。这少爷没诓她,真提起剑,加入了铿锵行列。
爱惜生命的杜小丹没胆欣赏,只好闪远远去蹲青蛙马步,外加打一套秋落后来教她的拳。
破晓,彷佛眨眼,阳光便穿透墨紫,将世界染成白色。
鼻腔吸进清晨的新鲜空气,杜丹目光没焦距地看着数月如一日,却又随着日升月落、四季更迭悄然变化的画面,迎着徐徐微风……忽然有感。
她心想,轻功会失传不是没道理的,古人的生活真的很单纯规律。自己上辈子生活看似多姿多彩,飞遍世界各地,走遍各国繁华,但除了一瞬的惊艳,以及留在数位相机里的定格画面,心里留下的,仅有模糊苍白的感受。
不像现在,光是眼前院落,自己就能品出诸多不同。
她知道哪些花草分别在什幺季节,会有什幺变化,知道他们成长到衰老的模样,知道院里泥土的触感及味道。
她亲手打点这院落,就连自己时常坐着的那块大木头,上头的年轮,她都仔细研究过。
因为慢活,因为简单,因为专注……她好像能感受到每样物品的呼吸吐纳,感觉自己与他们共存。在上辈子,她大概只能感受到空调的送风吧?
但在这,就连一阵微风,都是大自然的恩赐,都值得她闭眼细细体会及感动。
这瞬,她的心静了,彷佛明白了什幺。
“丹丫头。”
听见呼唤,杜丹飘远的心思终于收了回来。
“来了!”
神游不过眨眼,太阳竟已冒头,东方穆谨额上渗汗,她又打了盆水回房,让主子擦汗洗脸,才又开始一天的日程。
日复一日,除夕,新年,冬走春来。
枝头又抽绿芽。
转眼,东方穆谨主仆五人来到蒋府也满一年了。
“丹儿,妳可知自己生辰?”
杜丹悬腕勾画的动作未停下,抽空答道:“杜丹连父母何在都不知晓呢,怎幺会知道自己生辰?”
“以前的事一件也记不得了?”
“是呀。刘妈说我那时撞破了头,流了一地血,我醒来后便什幺都记不得了。”
“妳可想寻妳双亲?”东方穆谨坐在离她一段距离的椅上,手里把玩着玉佩,随意地问。
“不想。”
“为何?”
杜丹眼神凝重地盯着眼前画作,屏气凝神地落下最后一笔,吁出口气。
“刘妈说我在杜家口那孤身行乞,身旁无长,我那时被刘妈抓了去,至少也有个把月,若我有亲人,想必早已寻我去。可直至今日,依旧是没人寻过我,咱在蒋府不难打听,我想若非我已无亲,便是亲人有什幺苦衷不能来寻,或是不想要我了。”
东方穆谨沉吟一会儿,见她目光清澈,对自己可能被抛弃的这件事侃侃而谈,没半点悲伤,说道:“也罢。”
他本想,若这丫头的父母还在,或许能扶持这家子,无论是务农或从商的家底,怎样也比孤女的身分强,可既然这丫头无心,便不强求了。
他将自己的想法与她说明。
杜丹听完笑了。“少爷,咱自己一个也挺好,没牵没挂的,比起拖家带口的可轻松多了。”
“妳现在是好,以后若是嫁人,没娘家撑腰,被欺负没门哭去。”
“嗟,就不嫁呗!”
“就是不嫁,没家里撑腰,在外也容易受欺。”
“咱倒不这幺认为,若家里不合,一个人再好,也要被家里拖累。就算有娘家,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夫家不善待,娘家又能如何?”还不是赌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