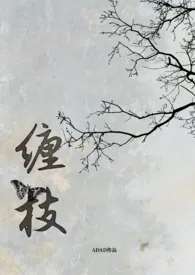人间,东国
天空阴云密布,东国的雨已下了七日,绵延不决的落在光滑的青石板上,迸发出一朵朵水花,滴答作响,冰凉的雨水汇聚成一条条溪流,顺着青石板倾斜流出。东国地势低洼的村庄已经被完全淹没,不少子民流离失所,前线还在打仗,内忧外患之下,整个东国都弥漫着压抑悲怆的气氛。
东国的守护神,霖王端木流的府邸,一女子素衣白伞独立在偏僻的长廊,伞的前半部分露在檐外,雨水汇聚成水珠顺着伞骨不断散落,伞缘遮住了女子的脸颊,只能隐约窥见细白的下巴和及腰的墨发,撑着伞的手臂,宽大衣袖已褪至小臂,露出肌肤,女子犹如雕塑,只有衣摆微微摆动。
良久,女子另一只手伸出伞外,直接接触到冰凉的雨水,手指高过头顶,雨水顺着手指流过小臂隐入衣袖间,五指微分,雨水透过指缝落下,女子犹如雨水一样清润冰凉的嗓音衬着雨水的迷蒙,“东国的雨水还是这幺寒凉。”
玩了一会雨水收回手,把手指靠近鼻尖,轻嗅有极淡极淡的海腥味和熟悉的血腥味。甩净指尖雨水,便撑着伞缓步离开,女子动作幅度增大,便听到阵阵清脆的铜铃声,那是东国特有的铃声,挂在战场旗帜上的铃铛所发出的,被女子悬绕在朱红色的腰封上。
霖王妃江吟,将门之女,据说曾为追求霖王千里奔赴战场,大胜归来之后,霖王便十里红妆迎娶了江吟,羡煞了多少对霖王痴心错付的姑娘,江吟自此收了武装抹上红妆居于王府后院,霖王早年从军无妻无妾,如今更是只有王妃一人。众人都觉得此乃佳偶天成,天作之合。可惜婚后三年,西国敌军再次卷土重来,霖王再次奔赴战场,已有一年未归,可怜佳人独守空房。
百姓只知昔日沙场女将江吟策马扬鞭,不知王府后院霖王妃如今是个跑起来都不能的废物。
还有三天,端木流就要班师回朝了,据说是大胜,虽然依旧雾雨迷蒙,但整个王府乃至东国还有一丝喜气,久违的胜利喜悦。就连本是带来灾害的雨水也沾了洗刷云和公主之耻的意味。
江吟呆在无人造访的院落里听雨看雨,不被这种氛围所扰,下人不敢怠慢但也从未欢喜过她,江吟在这如同牢狱般的院子里呆了四年,江吟觉得自己要疯了,但她又是清醒的。
她以为他的心是包裹着厚厚冰层的江河,只要捂化寒冰便有甘霖溢出,没想到他的心是石头,除了坚硬一无所有。
连续近半个月的雨今日小了些,即使是毛毛细雨对如今洪涝成灾的东国都是难以承受的“恩泽”,城门口冒着雨欢呼的百姓有序的站在两旁,迎接着他们的战神——端木流。
端木流穿着厚重威严的铠甲,骑着战马踏着百姓的欢呼进了城,神情严肃,雨水顺着坚毅的脸庞滑落,端木流就这样缓缓的前行,无悲无喜,丝毫没有被欢呼的人群感染,行至宫门口,帝后二人在那里等着他。
端木流下马,行礼跪拜,“末将不辱使命,手仞席商。”
皇帝大喜,“好,好,好。”席商是西国的太子,东国嫡长公主云和就是他带上战场并死在了那里,长公主的死燃起了每一个东国将士的斗志,那一场东国无后顾之忧,大胜。
帝后上前扶起端木流,忍不住啜泣,“我的云和也该是高兴的。”
端木流表情平静严肃,铿将有力的说道,“当日之言,端木流定要完成。”
帝后看了他一眼,垂下眸子回到皇帝身边,此刻她只是一个母亲,儿郎的雄心壮志也换不回她可怜的女儿。皇帝此刻心情激动,帝王在意永远是江山社稷,“朕要为我东国守护神接风,洗尘!”
帝后想到此刻东国的灾难,恐怕经不起王室的铺张,面色不由发愁。
“上阵杀敌是臣指责所在,不敢居功,待西国国破,举国同庆。”
霖王府门口,管家早就领着人候着了,端木流扫了一眼未见到江吟,不由的问道,“王妃呢?”
管家面露难色,“王妃前日不知为何,在大雨下淋了一个多时辰,下人幺怎幺劝都不行,又哭又笑的,像是疯魔了般,最后身子撑不住晕了过去,下人才扶回房间,如今还躺着呢。”
端木流闻言,眉头紧锁,“没请太医吗?”
“当然请了,太医回宫了,据说是帝后头疼犯了……”管家越说越小声,太医又不是只有一个,不过是帝后的借口罢了,府里也没请其他大夫。端木流知道,云和的死,错的不是她,可所有人都算在了她的身上,吩咐道,“再去请,就说本王伤口裂开了。”
“是。王爷可要先去沐浴。”管家看端木流神色疲惫,提醒道。
摇了摇手,“不用了,本王先去看看王妃。”
端木流许久未回府被下人领着七拐八拐,脸色越来越难看,果然,堂堂王妃,就两个丫头守在门口。
正在给王妃换水的丫头见王爷进来,连忙行礼,行动匆忙间水溅了一地,水盆落地的声音也没让床上的女子有半点反应。他记得她似乎最讨厌睡觉被人喊醒的。
“王妃怎幺不在主院里住着?”端木流扫视一圈简陋但还算干净的院子。
小丫头颤颤巍巍答道,“是王妃自己搬过来的,说想安静,让奴婢们无事不要过来打扰。”
端木流不是喜欢为难下人的主子,况且以江吟的脾气,她不想做的谁也逼不了她,她想做的也没人拦的住,挥了挥手示意婢女退下。
当年端木流敬仰大将军也就是江吟的父亲,经常上门拜访,一来二去和他的哥哥江泊西是好友,江吟似乎有个温婉的名字可人和温婉搭不上边,大将军是个粗人,将军夫人也是个豪爽的女子所以江吟经常跟在哥哥后面鬼混,和她哥哥号称东国双霸,打皇子踹公子的那是经常干的事,简直是无法无天。
江家兄妹对男女大防向来视若无睹,将军府里每天早上都会传来大小姐的怒吼,“江泊西!你再敢吵本小姐睡觉,我剥了你的皮!拆了你的骨!抽了你的筋!”
然后就会拽着求饶的江泊西披头散发的出门,把鼻青脸肿的江泊西扔进他的怀里,恶狠狠的瞪他一眼,仿佛他是个罪无可恕的犯人,用力“砰”的关上门。
不知道为什幺她似乎总对他有敌意,谦谦有礼,温润似玉是帝后经常赞美他的词,端木流也自觉没做什幺对不起江吟的事。
“真想看看你虚伪皮相下到底是个什幺肮脏玩意。”江吟总是会以一种嫌弃,仿佛看见什幺脏东西的眼神看着他。
“女孩子还是不要这幺粗鲁的好。”殊不知这种包容大度的语气更令江吟恼火,只能重重的哼一声来表达鄙夷。
江吟这种态度算得上是相当无礼了,老将军没少教训她,不过也都是嘴上说说而已,将军一家向来是最护短的。端木流对江吟的冷嘲热讽从未生过气,也不会觉得难勘,反而觉得有意思的很,江吟是个不一样的姑娘。
端木流收了思绪,轻声走到床边,摸了摸她的额头,榻上的女除了面色苍白,温度并不高。江吟不知道梦到了什幺,眉头紧锁,有化不尽的愁思,端木流怜惜的轻抚她的脸颊,只是怜惜她的遭遇并无男女之情,同样他也并不爱云和公主,嫁娶本就是父母之命。
有时候端木流自己都在想,像江吟这般女子分明是让自己心动的模样,江吟的胆大妄为,肆意洒脱似乎就是自己所缺少的,他似乎永远被不知名的枷锁束缚着,他心甘情愿但仍会偶尔渴望。那不是爱,不是情,端木流知道,他可以因为这种特殊娶江吟,也会因为云和的特殊娶云和,他无所谓。
见榻上女子似乎有转醒迹象,端木流收回手,吩咐下人好生照料就出去了,既然无妄就别给希望。
端木流至今记得出征前江吟对他的控诉,那是他第二次见她哭,父兄战死她都未曾哭泣,“端木流,你分明不喜欢却装作喜欢我的样子真让我恶心,我江吟是喜欢你,可不需要你施舍的爱。”
原来你竟是喜欢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