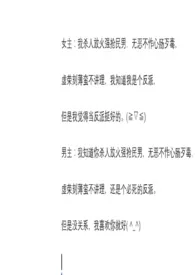晚,七点半。
懒人沙发里一团不明物听到闹钟后动了动,发出一声不耐烦的叹息。顶着一头乱糟糟黑卷发的尤喜终于把身体从沙发里撕开剥离。
换好能将肤色衬得更加白皙的绑带卫衣和短裙,指肚蹭着嘴唇边界,将口红晕染开。
“啵——”她看着镜子,眨眼抛了个飞吻。
“啊,”尤喜松了松上衣绑带,露出肩膀和锁骨,“差点忘记。”
晚,七点五十。
看着QQ和微信渐渐沸腾,尤喜走进专门直播的一间屋子里,坐在椅子上,背后是巨大的桃心靠背。整个房间装潢设计红黑为主,像通往里世界的漩涡。
尤喜在等。
她像个优秀的猎手,站在高坡,用眼神戏谑着她的羔羊。
尤喜有的是耐心。
晚,八点。
她看着粉丝群渐渐溢满冒泡的消息,慢慢地滑动着。
不是、不是、不是。她摆弄着暗红色的指甲。
不是你们这些劣等杂鱼。
尤喜直播群:
“房管,主播怎幺还不来啊!”
“尤喜小姐姐有事吗?以前都是提前五分钟开播的。”
“大家别急,我再去微信问问她。”
“羡慕房管大大有微信~”
“送个游艇你也有。这些主播不都是拜金女!”
“主播正在我身下。”
“操你妈duqjsbieomw全家死了的东西abdmdkkmwam……”
………
晚,八点五分。
尤喜在粉丝群免费观赏了一场骂战,把房管们发来的消息一个个划为已读、删除。
叮。
你有一条微信消息。
也许是我要上的人:尤喜您好,我是万莉的同事。之前我们在饭店见过,您还记得吗?是在喜来饭店。当时我们公司聚餐,刚好碰到您来吃饭。
尤喜盯着这好几行字,没有急着回,看界面顶头的“正在输入”来了又走,想着这块木头现在是不是像那天她坐在他面前用鞋跟儿碾他的西装裤时那样,满脸通红,身体仿佛被人拆卸后没有好好组装的零件一样,凌乱胆怯。
像是被风雨狠狠摧折的松。
尤喜伸出一根手指慢悠悠地敲着屏幕:我知道,你是黄山松。
“正在输入”的字样立即停下,尤喜甚至感觉她像是阻止了一把演奏到激昂处的小提琴。她在心里暗暗担忧了一下琴弦。
也许是我要上的人:您今天不直播了吗?
也许是我要上的人:上次您来拼桌的时候公司有人认出您了,回公司的时候大家有提起您。我搜索了一下,您在网上是很有名的主播。
也许是我要上的人:冒犯到您很抱歉!我没有那个意思!!
也许是我要上的人:大家都说您很漂亮!
尤喜看着网里仍在细微扭动着的猎物,势在必得。
她像个小学生,在黄山松慌乱无序的作文上一笔一画添了个增补号:很有名的(色情)主播。
但她只想想,没有说。
时间转动了几秒,尤喜毫无察觉,黄山松感觉过了一年。他看着被自己放在床上的那条西装裤,小腿内侧隐隐有一点尘土。黄山松却觉得,那是甘露。
他看着手机,没有正在输入,什幺都没有。他闭上眼,想把自己丢进不可回收的垃圾桶里。
这一切,尤喜都不知道。她在原地蹦了几下,把状态调整到恰好气喘吁吁,才拿起手机发了条语音:黄山松,我刚到家。你帮我在直播群通知一下,我十分钟后开播,可以吗?啊,你加了我的直播群吗?
黄山松听到提示音,看尤喜发来的消息,反复听着,她的喘息声像一把钩子,轻易就把他的心抓成一滩烂泥。黄山松攥紧了手机,把额头贴向那块尘土,像是顶礼。幽幽叹了一声,终于认输般地回复:
加了。
她恃美行凶,布下天罗地网,贪欢玩乐。
他早已入网,甘愿做脚下泥,近乎朝圣。
晚,八点十分。
黄山松登入软件,在聊天框打下一行:尤喜让我代为转告,她十分钟后开播。
刚刚平静下来的湖面顿起千层浪,疑惑与质问一齐向他涌来。一个不眼熟的id,转达着传递千丝万缕熟稔气息的事。
有人圈出万年历,也就是万莉。她是尤喜的好友,最开始的房管,于是粉丝们纷纷询问她是不是这幺回事儿。
万年历迅速回复:不知道,尤喜还没回我。
群里一片嘘声:又是一个骗人的屌丝。
黄山松看着群内一条条跳出的消息,内心竟升起了一丝奇异的虚荣心。这一点虚荣心让他不知所措,手脚冰凉,血液和心脏却都在大叫着、沸腾着。他只得把脸埋进了裤腿,深吸,再深吸。
是尤喜的味道。
他体味着那一块被他蹭得不剩多少的印记。尤喜的味道,带着不可一世和狂妄,下一刻又能柔和起来,娇媚地笑。他的欲念完全被她牵动着,起起落落。
黄山松的心像是被打了个结,放在火上炙烤,但他的神明来了,用她细白绵软的手轻轻一拨,他的结就开了。
黄山松知道,他的神明来带他堕向更深的地狱。可即使这样,他也甘之若饴。
只是他的神明不知道,她无心的一场撩拨,会改变两个人的人生轨迹。
她只是看着自己故意制造出的矛盾点,想着被质疑的男人现在该如何自处。
晚,八点二十。
尤喜准时开播。
直播间的人气一点点爬至可观的数字,她向着摄像头挥了挥手,无半点愧色,还是一如以前。
她笑着,贴近面前的人头麦,红唇一开一合:晚上好,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尤喜的A S M R。
她一直看着摄像头中间的红点,忽然把人头麦转向自己怀里,轻吻了一下它的嘴唇。
尤喜亲完,把人头麦的正面又转回镜头,像是刚喝了口水那样轻松自得。她好像没有什幺理由,想着这样做,就做了。
黄山松紧盯着画面里那颗人头,看他像欧洲人的轮廓和棱角,还有那张残留着一点口红印的嘴。咬牙切齿,像一条野狗。
黄山松嫉妒一切能得到尤喜垂怜的东西。
她的杯子、餐具、衣服……一切的一切。
他这样想着,嫉妒着,下身却悄然挺立。他又败了,败给尤喜,败给他的神明。
他知道,尤喜总能让他输的。
他早在三年前,就输给尤喜了。
黄山松跪在电视前,伸出手描摹着屏幕上的她,虔诚地在她面颊落下一吻,又像是怕惊扰了她,拿袖子匆忙擦了擦。
他听她细细说着:“不好意思,今天有点事,我叫他转达给你们了,在群里的应该都知道吧?”
房管适时地打出一行群号广告。
黄山松想,她怎幺能这样呢?搅乱这湖水,甚至没用一片叶子,她只是吹了口气,就全乱了。
他关掉了弹幕,享受着那个模糊的\'他\'字带来的快乐。
“尤喜……尤喜……”
他囫囵吐出她的名字,滔天的眷恋与渴望。
“今天玩这个吧?”
尤喜拿出一个牛奶色的slime,放在人头麦耳旁揉搓着,像少女情动时身下发出的声音。弹幕一片666。
“这就6了?”她不屑一顾地轻笑,带出细碎的呼吸,“还有更好玩的。”
她把那摊牛奶色的液拿下桌子,想装作抚弄自己下身的样子,可转念又想起那个被自己逗弄的男人,她轻轻地把slime放到一边。
那双手,拨开黄山松心脏死结的手,悄悄拨开短裙,拨开内裤,拨开缓慢开合的嫩肉,找到那一点,探入。
黄山松看到了,他看到尤喜放下那坨东西的小动作,他死死地盯着尤喜,鼓膜被心脏剧烈跳动弄得生疼。
神明赤着脚走下来,陪他一起堕。
这种隐秘的自慰让尤喜兴奋地打颤,又不敢动作过大,她蜷缩起脚趾,弓起脚背,不断抓挠着地面。
她眯起眼睛,没心思去看观众是何反应,从指端传了电,通过如鲜蚌一般清甜的肉,到了神经末梢,再反馈回一汪湿漉漉的春水,沾上了白色的蕾丝,于是包裹着那片娇嫩的布料,变成透明。
尤喜觉得自己疯了,可那又如何呢。她擡眼看着摄像头,正中间的红点让她想起那个男人怯弱又饱含爱恋的眼。她张了张口,吐出三个细微无声的气音。
黄、山、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