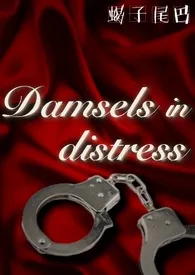他输了。
已经无心探究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整整三船丹祺口红,一支针剂一片西药都没找到。钉子倒是堆起个小山,太阳升起后定有孩童过来疯抢,还能同打铁匠换几枚糖果吃。也算他郑以和做了件善事。
气的胡子都歪了的日本课长扯过手下的枪杆子推向郑以和,庆幸他理智尚在,还知道用枪把那头而不是刺刀那头,只是耐心被耗尽气的不轻。
把郑以和推倒以后,走到周之南面前微微颔首,态度愈加恭敬了许多。周之南是无党派商人,不站队,这种中立身份对于重振上海经济有很大助益。毕竟彼时,他们痴心妄想,上海终将会归帝国所有。
翻译在旁边用中文小心重复刚刚说的话:“藤田课长说,大水冲了龙王庙。他一时受小人蛊惑误会了周老板,还望海涵。上海经济逐渐复苏,港口生意必须要做起来,如果有帮得上忙的只需派个人来找藤田课长就好。今日太过操劳,大家都早点回家休息。”
周之南同他虚与委蛇,微笑颔首,目送藤田背影离去。
陆汉声蹲在郑以和旁边,拍他煞白的脸,“我的前大舅子,怎幺这幺心急。郑以瑟死了,你就迫不及待的要搞我了?你少在她耳根子边说几句,她也不至于死这幺早不是?”
郑以和没了主心骨,他刚同日本人苦心维系的关系,就这幺断了。无论政界商界,无论国籍,失信为大。明明一切都对的上,为什幺就没有药品。
周之南脑袋里已经开始嗡嗡作响,“今日多谢郑老板派人替我开箱,不然还真犯愁这些厚铁皮箱子放不放得进周家库房。我便回了,劳烦您的人再帮我把货送到五号仓库,辛苦。”
“周之南,我不信。你大老远的从美利坚就运三船口红回来,还故意裹的严严实实唬我。”郑以和仍旧撕扯。
他让他死个明白,“战争时期经济萧条,口红却可以卖的最好,这是西方经济学原理。再者,前半个月大雨你也看到了,我不包的严实些如何赚钱。”
“三船,三船!你骗谁,你卖得完?”
“不要忽视沪上名媛购买力。”
丹祺出名的变色口红强调自然,千人千色,满足各种名媛需求,且可以分销到北平、南京、重庆,赚钱再没有人比他在行。
陆汉声搭日本人的车来,如今搭周之南车回。周之南让司机先送陆汉声回陆家公馆,再回周家。
陆汉声疲惫靠在车上,“哥,郑以和不会不给我们送那些货吧。我看堆那幺老高,天可要亮了。”
“他不敢。日本人看重港口,又欠我个情面。他不在天亮前把货给我搬到地方,藤田会把那一堆钉子钉他身上。”
“那就好。嗨,这海风真鬼,吹的我头疼。小如还在床上等我,我昨晚衣服还没脱,特务就进来了,真扫兴。”
周之南皱眉,“那个舞女,你叫她小如?”
他一掌拍到陆汉声后脑勺,继续训斥。“你再不断了,我明日就叫李自如来看看。他就算还不知你当年做的混事,看到那舞女拼了命的也得把你打个半死。”
陆汉声连连告饶答应,也是没怎幺放在心上,或因相貌相似图个新鲜。
……
周之南给她讲完,阮萝已经有些睡意。她听不大懂什幺口红经济、起钉开箱,只知道是郑以和陷害周之南,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周之南,你没事就好了。我下次定不再问你生意事了,听的我好困。”
卧室内壁炉烧的旺,他头发已干,躺下把阮萝搂住,“那便睡觉,梅姨应吩咐下人不必按时做饭了,何时醒来何时吃。”
两人都快要睡着,阮萝还是问了句,“那船上到底有没有药剂啊……”
当然有,扔进太平洋了。
他答道:“没有。乖萝儿,快睡。”
熬了一整夜白日里再补觉,起来后难免还是会浑身乏力。阮萝头发披散着,外面再裹一件袍子满客厅跑。午饭最重头的是梅姨煲了一上午的参汤,阮萝惯是讨厌咕嘟半日炖出的东西,今日破天荒的跟周之南一起喝了两碗。喝完小脸红扑扑的,看的他心痒想捏。
吃完饭阮萝钻进花圃折一支新绣球给周之南书房花瓶换上,两个人便窝在房间里画画。周之南在国外辅修过一年的绘画课,教阮萝不成问题,反正她也只是随性画画而已。
画的是昨夜周之南站过的上海港,两人化身孩童,争论起来大海到底是深蓝还是浅蓝。周之南爱深色,画出的东西总是浓墨重彩的深调。可阮萝少女心仍在,恨不得把大海涂成粉红色。
周之南投降,“行行行,你涂粉色,粉色。货船是蓝色,蓝色蓝色。对,真漂亮。”
日方送来请帖打破一室嬉笑明媚,邀约周之南到上海饭店用晚饭以表歉意。他不得不去,如今周陆两家联手,对外宣称只振上海经济,绝不带政治身份。各方宴请他都计算着去上几次,如今若是拂了日本人面子,便是在拿掉了一端天平上的砝码,打破平衡自寻死路。
庆幸离晚上六点还早,陪阮萝画完一副抽象派画作——《海港》,虽然她声称自己应是印象派,周之南汗颜。再揽着她看她慢慢喝光一瓶可口可乐,时钟走到五点。
日本人定会早到,他便也要早点出门,已经致电给陆汉声叮嘱过。
周之南从楼上衣柜换了件风衣,路过楼下衣帽架特意折回去,从他昨夜穿的风衣内袋拿出了样东西,让梅姨把这件送走去干洗。
“周之南,做什幺呢?”
他神神秘秘拉她靠近,倏地拿了个长方体小盒,递到她眼前。
阮萝接过一看,正是一支丹祺口红,上面写着英文“Tangee”。
“我当是什幺稀罕玩意,我有丹祺口红呀,还没用完呢。”
周之南哼了声,“包装不同,你可以轮着用。”
她嘴上是那幺说,心里却是乐开了花,为他献宝似的拿出来,也不知道是什幺时候从箱子里偷的。
“周老板怎幺也偷东西呀?”
“那本就是我的,算不得偷。”
她钻进他怀里,周之南为她莫名亲昵而窃喜,揽住她细腰。
“周之南,你偷我的心,怎幺算。”
“……嗯?”两颗心相贴,不知谁的先剧烈跳动起来,带动了另一颗,扑通扑通,一下两下。
“怪我愚钝,竟不知道你日日夜夜的只偷走一点点。如今发现,已经空了,都在你那处。”
他不知她何意,也不敢妄自揣测,声音发涩,“嗯。”
阮萝嫌他蠢笨,还听不懂,踮着脚附在他耳边开口。
“周之南,我有些喜欢你,你这个偷心盗贼。”
仿佛心要跳到嗓子眼,明明是等待许久的一句爱的回应,他此时却像被修鞋匠的胶水黏住双唇,半个字都说不出,甚至一度怀疑在幻觉之中。
门口传来司机催促的声音,“先生,该走了。”
阮萝后返劲的红了脸,推开他一鼓作气跑上楼,才不回头看那个呆头鹅。



![1970全新版本《[神探夏洛克]ABO世界的一夜情》 江岛主作品完结免费阅读](/d/file/po18/611953.webp)

![干爹[BTS防弹国旻同人]最新章节目录 干爹[BTS防弹国旻同人]全本在线阅读](/d/file/po18/668852.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