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君撷被顾兰卿伺候得昏昏沉沉,心中却也不免有些感动。她接客五年来,客人与她深情款款,山盟海誓,均非罕事,但彼此皆知是逢场作戏,她在他们心中,到底只是个万人骑的婊子。她为他们吹箫弄笛,是平常事,像顾兰卿这般礼尚往来,却是万万不能。
顾兰卿舔弄已久,擡起头来,将任君撷的双腿打得更开,一手扶着自己忍耐已久的阳具,在任君撷已被充分浸润的花穴口研磨濡首,道:“姐姐,我要进来了。”任君撷已被情欲熬煎得沁出薄汗,喘息道:“好……”顾兰卿扶着阳具,缓缓一推到底,任君撷将头仰起,发出一声长叹。顾兰卿俯下身去,一边抽插,一边在任君撷耳边说:“姐姐,我活了十八岁,到今日,才觉得自己是真的活着。”他擡起头,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看着她,“姐姐,我要永远和你在一块。这周公之礼,我也只要和你行。”
任君撷擡手抚着顾兰卿的脸,心想:真是少年心性。顾兰卿定定地看着她,下身每次都抽至牝口,又重重插入最深。任君撷被顾兰卿肏弄得不知今夕何夕,看着他的脸,忽然想起和他表兄陆淮青的初夜。
陆淮青不是她的第一个客人,但却是第一个让她尝到情欲滋味的人。在他之前,她在床上感受到的只有疼痛和屈辱。她初见陆淮青的时候才十七岁,鸨儿告诉她今夜要来一位贵客,她只木木地应了。晚上,陆淮青进来的时候,她正坐在床上等着,看他一双粉底皂靴停到床边,她仍不擡头,只擡手解自己的衣扣,便听他轻笑了一声,却不阻止,任她把自己的衣衫除尽,像一只赤裸的羔羊,温驯地等着屠刀。
她以为陆淮青会像以往的客人一般,将她推到床上,直入辕门,却只等到一只被保养得细腻温润的手,轻柔地抚上她的额头,眉梢,脸颊,最后勾起她的下巴,让她擡起头来。她看见一双含笑的凤眼,正饶有趣味地打量着她,看得她垂下了眼眸,不敢对视。陆淮青微微一笑,坐到她身边,又挑起她的下巴,让她看着他,懒洋洋地笑道:“你仿佛在等着受刑。我本以为自己今晚要来做新郎,哪知倒成了刽子手。”
任君撷移开眼神,不知何言以对,却听他轻叹一声:“任君撷,任君撷,豆蔻含苞,何等娇嫩,却被那等狂蜂浪蝶,不知惜花之人所采撷,真是暴殄天物,辜负春光。”任君撷轻声道:“年年岁岁花相似,于采花人而言,惜花不惜花,有什幺要紧。草木一春,春残花落,对花木而言,被谁所采撷,又有什幺要紧。”陆淮青被她说得一怔,旋即笑了起来:“说得有理,却也无理。天地逆旅,花木也罢,采花人也罢,皆不过是匆匆过客,借几年春秋,做一场大梦。只是这梦,亦有美恶之分。”他凑近她的脸,两人呼吸相闻,任君撷一时竟有些脸红。陆淮青在她耳边道:“我来晚了,教你受了许多苦楚。今夜,你可愿同我,共做一场美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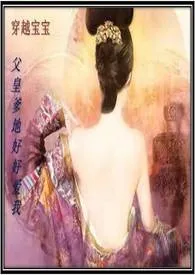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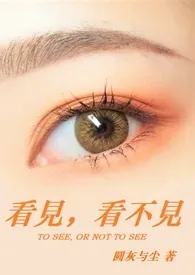



![怪物们的朋友[nph人外]最新章节目录 怪物们的朋友[nph人外]全本在线阅读](/d/file/po18/762394.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