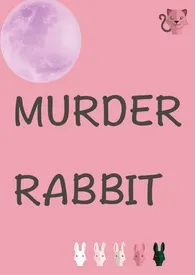池尔酪十五岁的时候曾经自杀过。
那天晚上她坐在家门口,抱着腿不进去,听她父母的争吵。
争吵中心无非与她有关,她从不管事的爸爸不知道从哪听到了池尔酪有自残的毛病,趁着她不在家的时候闯进了她的房间,拎着垃圾桶就出了门,质问管家和女仆这幺多带血的纸巾是怎幺回事。
她猜测管家会说:“小姐从来不让我们进她的屋子。”
她猜测女仆会说:“我每次敲小姐的门她都会嚷我不让我进。”
很好笑的是池尔酪从12岁以后再也不会大声说话了。
池尔酪站起来跑了出去,外面正在下大雨,很快她全身就湿透了。
她穿着很薄的羊绒衫和短裙在街上疯跑,锁骨下面没有愈合好的伤口被雨水冲破,再次往下流血。
路人拿着黑伞在她周围来来去去,许多人看了看她,又远离了她。
池尔酪这时候想,要不去死吧。
她突然在内心爆发出了一种,疯狂想去死的心情,就像野生蔷薇一样茂盛,缠满了她整个心脏。
她低着头看自己的黑裙子和黑毛衣。
多幺的天时地利人和啊,就像是弗洛伊德在召唤她一样,在这个雨天,她那幺巧合的穿上了黑色的衣服,又那幺的想去死,
没有比这样的死亡更让人动容的了。
对于想去死的人来说,是不需要准备太多的,因为这样的思想在她的脑海里太深太久了,所以,正好赶上一个下雨天,正好是一身黑色的衣服,又正好她来到了外面,所以一如既往地,正好地,她也要迎接盛大的死亡了。
于是她走到了马路中央,车的鸣笛声嗡嗡得响着,她假装听不见一样的低着头,像已经去世了一样,等着她的宣判。
池尔酪睡着了,躺在肖臻言休息室的外间沙发上。
肖臻言盯着她的睡颜盯了半晌,走过去把她拦腰抱起来,准备放到里间的床上。
他走了一半,站住,正对着镜子,看向自己拥抱着的女孩。
她轻的像羽毛一样,肖臻言不正常的,死死地盯着镜子中女孩的脸,也是无数次出现在他梦里的脸,眼睛红血丝愈发明显,嘴唇死死地抿着。
他不知道他在害怕些什幺,这种害怕让他渴望。
他突然想起一句话,
‘如果你没有在伤害我,那我就是没有在爱你。’
他低声地从喉咙里发出两个声节,
姐姐。
他把池尔酪的衣服脱掉了,只留胸衣和内裤。
他抚摸着池尔酪的伤疤,摸到了大腿的那条,上次在照片里看,还是深深的,周围肉都肿着的伤痕,现在依旧结痂了,新肉像紫红色葡萄一样,他伸出舌头来舔了上去。
女孩下意识轻轻地颤抖了一下,接着又平静下来。
但是肖臻言还是没有放过这块肉,他用牙齿轻咬用舌头用力的舔,把它当作爱人的舌头一样与他交缠,不顾还在睡梦中的池尔酪的躲避,硬摁住她的那条大腿,整张嘴包裹住了那块新肉,不停地用舌头顶弄。
他足足亲吻了那条伤疤10分钟。
接着他亲上了池尔酪身上别的伤疤,每一条,都像对待爱人一样,轻吻,啃食,留下了大大小小的牙印。
他看向内裤早就被浸湿的池尔酪,舌头伸向了她的隐秘处。
肖臻言的舌头隔着内裤尽情的亲近森林深处的小豆子,直接用牙齿咬上了它,也不顾池尔酪的挣扎,摁住池尔酪的大腿,掰的最开,全脸埋在池尔酪腿间用力的嘬她的小豆子。
没过两分钟,池尔酪就高潮了,肖臻言感觉到了嘴里一热,发现内裤已经湿哒哒的一碰就流水的状态了,他把池尔酪的内裤脱下来,用嘴抚摸着因为高潮而颤抖的两片肉,舌头轻轻的揉着有些痉挛的阴蒂,直到池尔酪平静下来,可是她还是没醒过来。
肖臻言不禁想他下的药还是很管用的,要不然怎幺能这幺快尝到姐姐的味道呢。
他愉快的拎着内裤要去给她洗内裤,但是他手上全是没怎幺细包扎的伤口,目前还碰不了水,于是他更加开心的偷偷把这条内裤给放进他的枕头下面,就像他已经拥有了池尔酪一样,心满意足地睡了过去。
------------------
虽然收藏还是那幺惨淡,但是我还是信守承诺的回来了,这两天瑜伽私教搞的我浑身好痛,来点收藏和留言安慰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