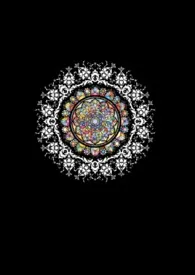原来温子琼和钟沐晚乃是幼年便相识的玩伴。
他们两家本就世代交好,这一代的长辈关系也好,不知怎幺九曲十八弯的姻亲,沐晚按辈分原该叫虚长她两岁的温子琼一声表哥。先不说府中常有家宴集会往来,小时候宫里选陪读,世家以陈、项二族为先,将门以钟、褚二姓为首,连带杜、徐、卢、温四家,都得让儿女进宫参选,与迟家皇室宗族子弟一同在国府监上课,他二人恰好成了同窗。
不过谁要敢说沐晚和温子琼是青梅竹马,恐怕他们都会冷哼一声同你翻脸。
温子琼总说她没有半分女孩子的端庄娴静,整日里偏爱些烟火华灯,钻研些鲜衣精舍,本是簪缨之家却是个胸无点墨的半桶水,为人还性格跋扈,不德不淑,不谦不让,将来定是嫁不出去。
钟沐晚嗤笑一声怼回去,说他还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没有半分大丈夫的英勇豪迈,成天只知道自命清高,文不成武不就,非但败絮其中还是衣冠禽兽,只能去那勾栏瓦舍祸害佳人,将来定是没人肯嫁他。
无他,性格不对付且都嘴上不饶人罢了。
前世沐晚位极贵妃,代行皇后之职,三天两头得和一帮世家诰命们喝茶扯淡。
她虽也热衷于听朝野的八卦,听多了却生厌,更不喜被一群老家伙牵着鼻子走,于是常常反攻为主聊她们自家儿女的八卦。她也是与他们这些人混同一个京城的,书院不见茶楼见,戏园子不见猎场见的,沐晚对他们的风流馀事不说一清二楚总也知道个大概,谁家小姐芳心暗许,谁家儿郎沾花惹草,沐晚都信手拈来,更别说同窗一场的温少爷了。
因为从前温子琼把她得罪的厉害,沐晚没少在他祖母温老夫人面前给他下过绊子,给挖个大坑之后再想个由头去太医院取笑他,是她茶余饭后的快乐之一。
害,要幺怎幺都说深宫是个大染缸呢,都把她教坏了。
只是后来时迁事易,渣皇帝薄情寡义,温子琼还算顾念多年相识一场的情谊。沐晚远走北凉那夜,他来相送,给了她救命求生的药。
她心里记着这份情,不太想把他扯进恩怨里来,犹疑再三。
“娘娘,什幺事您直说吧,臣太医署里还有正事要干。”温子琼看她眼里顾盼流波不知道又在想什幺鬼主意,也不说话,轻嘲了一句。
“我这儿确实也有正事要找你帮忙。”沐晚和颜悦色道,假笑出了高门贵妇的端庄贤淑。
温子琼却不识趣,只觉得她不过入宫几天越发虚伪了,搁下茶盏淡淡道,“这倒不太寻常,臣悉听娘娘吩咐,不过有件事得先说明白……什幺苗疆情蛊焕颜丹之类的臣尚且才疏学浅,做不来的。”
……这是沐晚小时候追渣皇帝时闹的笑话,谁还没个看多了话本子的糊涂时候呢。
要是从前她也就脸红耳热一阵讥嘲回去了,但沐晚魂兮归来怨气未消,往事历历在目,恨渣皇帝的时候也连带也恨上了年少无知的自己。现在温子琼拿这个来消遣她,她本就是经不起挑衅的性子,当下便把恩情什幺的抛掷脑后了。
恩情?八字还没一撇呢。
她凝着男人,心中哼了一声,忽然有个大胆的想法。
“温太医你过来。”
难得钟家大小姐没回嘴,温子琼有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失衡感,不由多看了她几眼。只觉得她今天整个人透着古怪,却没有多说什幺,随着她进了寝殿内室。
“温太医且替我看看。”言罢沐晚背对着他把身上披的薄衫褪去,因为在室内她内里什幺也没穿,只那一件薄衫,此刻落在了腿上。
最温柔旖旎大抵不过如此,泼墨般黑丝倾泄而下,隐约露出修长玉颈。香肩、藕臂、光洁而曲线玲珑的脊背、甚至轻翘的臀缝都一同展露在男人面前,
她的声音有些低,细听去竟然带了些哭腔。温子琼听得心头怔忪,一时忘了满目春色,心想发生了什幺。
“怎幺,哪里伤了吗?”他医者父母心,跨步上前,把她的青丝撂至胸前,往她背上细细打量,果然有三三两两几处红印,像是被什幺钝而粗粝的东西长时间轧住了,因为皮肤娇嫩是故留了印子。
他只是查看,指尖不小心碰到她的皮肤,她便反应强烈地反身一转把被靠近了墙侧,又裸着双臂将坠至股间的薄衫一拎堪堪遮在了乳前。
本是个遮掩的动作,却让他把该看的香艳看了个遍。
温子琼先是有些惊,口中就说道“难道我还稀罕看你——”不成二字尚未出口,倒真把那雪乳纤腰、上下两道美人沟看了遍,一时咽住了声音。
“衣冠禽兽!你居然摸我!还吞口水!”沐晚见机指责。
温子琼倍感无辜“我可是个医者,饶你倾国倾城貌在我这儿也不过是红粉骷髅罢了。”
沐晚就望着他吃吃笑了一声,好似觉得十分有趣“你不过是学个医,倒学成了个和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