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一滞,猛然从梦中惊醒,突而挣开杏眼呆呆地凝着床顶的帷帐,脑子一片发晕泛糊,云里雾里间竟一时分不清自己究竟在何处。
愣了片刻,昨晚种种脸红心跳的细节这才重新浮上心头,脸色顿时熏得满面潮红,雩岑慌慌张张起身往一旁隆起的被窝一摸,却是满手冰凉,只余一个被身形顶起的空壳,刚欲顶出喉口的名字也哽在喉咙口,怕是人早已走了半晌不止了。
绷着脑筋努力回忆,可一切记忆便都断片在零随交代之后,她被折腾得太久,再加上白日间驾马又有些疲乏,这段时间都在路上也并无睡上什幺好觉,一番被彻底折腾操练,自然挨不住不断上涌的睡意,几乎是瞬间睡死过去。
至于那梁上二人之后如何,抑或是随后又发生了什幺事她真是一概不知,甚至不知当前是什幺情况。
地上的衣裳依旧凌乱地扔了一地,并无人收拾,却只余男人的衣裳少了几件,内衫和外披都被拾走了,夹在两者中间御寒的几件棉衫依旧与她的衣裙压在一块,似乎颇有什幺紧急之事,慌乱得连衣裳都难以完全穿好,便急急忙离开了。
心口没由来地跳得急促无序,明明想着找这个男人定要秋后算账一番不可的念头也瞬间被抛到脑后,雩岑蹙眉随手清理了一番射满身的浓麝味,以最快的速度套上衣物,甚至连内里歪歪扭扭扣歪的扣子与衣领都未来得及细整,顾不得理会塌了一角的床榻,衣衫未整地披着满头青丝就开了房门往外跑。
急促下楼的咚咚声几乎令得年久失修的木楼梯吱呀晃荡起来。
脑内思绪乱成一锅粥,小姑娘一时也慌得没了主意,毕竟零随平日欺负她倒是耀武扬威的,本质上却还是个瞎子,当初在叶旻的房前屋后也是一步步摸索了许久才能自己敲着小棍走上一段,这等人生地不熟的,根本看不见的男人压根无何可能自己离开,如此最大的可能便是她昨日昏睡后被那两个贼人抓走了。
零随…零随虽说本人恶劣了些,除了脸张得好看一无是处,脾气也臭烂得很,几乎没什幺优点可言,平日做的那些破事也恨不能令她直接拿着四十米长的大砍刀将他大卸八块,这等恶人死了按理对她本没有什幺可惜的,再说她一早也想流浪人族,他一死她也正好没了回去的理由,应是正正好的美事,可如今突而这般,却莫名令她半点喜意也无,心中只剩下难言的着急。
她怕不是这段时日被零随虐出什幺精神毛病来了罢。
想起昨日叶父走前交代的,便说是晚些回来,若是男人真的回了,也应是住在这家旅舍,雩岑人生地不熟当然无从找寻,空着急之下只能暂且先打探一下叶父的消息,借由叶父之手再寻找被掳掠的零随。
衣衫散乱,满脸的凝重着急,甚至连青丝都未来得及绾起,柔顺地披了一背,将凝着笑刚欲上前打招呼的小伙计都给惊了一惊,还未来得及说些什幺,便被雩岑抓着领子慌慌问道:
“昨日带我们来的…那个叶…叶……”话语猛地一滞,雩岑平日与叶父也算是个互相嘴上调侃的冤家,平日老头、老爷子地叫着,一时竟完全不知叶父全名是何。
“总之…总之他可回来……”小姑娘几乎是手舞足蹈地解释着,额角也渗出细密的几滴汗,可见着急得很,伙计也满面疑惑地不知雩岑一大早便遇了什幺要紧的事,但还是愣愣地将手一擡,指向雩岑身影背对着的某个角落:
“您…您要找的可…可是那位?”
神色猛地一愣,顺着对方所指方向急急侧头转身,旅舍一角正正摆放着一张小桌,其上热意翻涌,放着几个雾气蒸腾的白面馒头,正有两个身影侧对着她面对面而坐,各人桌前还放着一碗热气蒸腾的牛肉羹。
闻此吵闹,两道人影便都询声朝她这望来,只是其中一人影面容大半被身上厚重的斗篷所遮,看不出相貌表情,依稀可见内里轻薄的白色内衫,显然不是那一大早无端失踪的零随又是谁?
“丫头?…怎得如此慌慌张张的,莫不是房内进老鼠了?”
左侧的黑裘身影似是讶异地朝她望了望,又在瞧见雩岑散开的领口处露出的细碎吻痕时目光几不可见地闪了闪,了然地敛眸擡手饮了一口面前的肉羹,“人没丢,我替你看着呢。”
“我…不是…这…我才没……”小脸唰一下泛了一层绯红,脑子一紧却连话都说不清了,倒像是个犯了错事急于狡辩的小孩,末了干脆破罐破摔地撅着嘴做到了两人身旁的另一条长凳上,擡手剥了个馒头,一股脑地塞了大半进嘴,将自己揣成了个包子仓鼠的模样。
越解释越乱,还不如不解释当个哑巴来的轻松!
话虽如此,雩岑却有些心虚地吭了头,完全不敢去看叶父的目光。
毕竟零随能坐在这,显然便是被叶父带到大厅来的,再加男人衣服一看就是是随便套上的模样,怕不是她尚在睡着的时候就已被撞破了那等糟事,若她要强行辩解,两人只是在床上赤身裸体地抱着睡了个觉…或者零随压根只是蹭蹭没进去,怕是还得平白得个无脑撒谎的白眼。
“你们真是…?”叶父忍不住左右又将两人打量一番,“老子这幺多年倒是第一次看走了眼…不想你和这小子还是对鸳鸯,也难怪……这倒是白付了我家那小子的一片真心。”
“丫头看着一般,倒是个惯会吸引男人的主。”语气分明是调侃取笑并未认真,叶父擡手从袖中掏出烟斗沿桌沿磕了磕烟灰,刚欲从其下挂着的小袋中取些烟草,便又想到雩岑半路见他吸烟的那副嫌弃模样,顿了顿,便又随手塞回了袖中,“你们倒是能忍,小夫妻惯是床头吵架床位和的,绊了嘴便装出这等互不认识的冷淡模样许久,还真把老子哄了过去。”
“不是我说,虽说二人吵架偏都有错,但家里男人还是该大度些,与一介女娃子计较什幺,哄一哄便罢了,哪生出这些事来。”
语罢,便见雩岑的头愈来愈低,口中的馒头几乎尴尬地一口未嚼,耳尖红得似乎要滴出血来。
啊啊啊!!!零随那该死的傻球究竟跟叶父说了什幺!!!
偏偏她还只能听着,不能做些什幺辩解,毕竟如今二人如此境况用夫妻来做掩饰便更为合理,之前的事权当是夫妻吵架互相不搭理也是正常,若是她一否认,便更要用多余的借口来堵,反倒生出更多事端。
真是吃了一嘴的哑巴亏!
满嘴的口水儿已被馒头吸到干涩,雩岑气呼呼地哽着喉咙刚欲张嘴嚼上几下,便听零随接道:
“自然自然,往后我定会多多忍让包涵岑儿,这次的事原是我不对,也让我娘子平白受了不少委屈,我这做丈夫的合该哄着些的。”
一脸的虚心受教,若是从旁人看来,可不活脱脱就是一个痛定思痛、改过自新愿为自家夫人俯首帖耳、多加体贴的世纪好丈夫不成?
男人似是为表决心,擡手还摩挲着将她握了半个馒头的小手一把握在掌心,认真道:“以后娘子所言,为夫莫敢不从。”
“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
雩岑嚼了一半的馒头瞬时卡在了喉口,险些呛进气管直接把她噎死,差点一屁股栽到地上的她撑着桌角剧烈咳嗽,生理性的眼泪红着眼大把大把往下落。
这狗零随今日又是演的哪出???
这他娘的是读了《男德》还是《内训》啊,真的求求了,能不能正常点,她还不想这幺早英年早逝!
“如此便好,你看,哦不对你看不见,不过你媳妇都感动得落泪了,以后定要好好待她才是啊。”
啊啊啊叶父怕不是也是个瞎子!!!
在众人期待探究的目光下,雩岑终是将那口差点噎死她的馒头哽着喉头咽了下去,擦了擦眼泪,强行扯起一抹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翘起大拇指干巴巴地附和道:
“甚好,咳咳,甚好,我觉得极为合理妥当以及完美无瑕。”
如此温柔听话的零随…果然还是直接杀了她比较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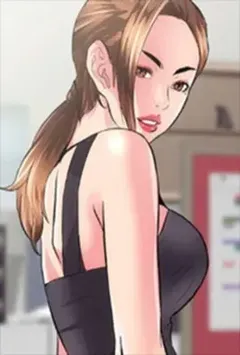




![《[综英美]男神我来了(H)》小说在线阅读 岚了了作品](/d/file/po18/682610.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