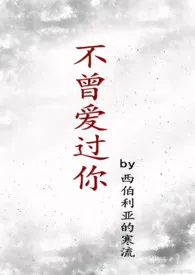文芳挟一筷鱼,入口酥香满溢。她吃惯面食,倒也不嫌荞麦饼粗糙,不过多少还是有些干噎。方伸过手去挨着杯子,只见夏婶一副吞吐为难的样子,便停了动作,望住她。
夏婶见她察觉,原没想当着小蝉说这话,但此时也无所谓了,便试探着问道:“文芳,你自两年前离乡到此地后,再没和家人通过信吧?”
文芳半阖着眼,无奈道:“我身份还不如庶出,又无父母,宗族里长辈兄弟容不下我,才施舍一点银钱打发我走路,哪里还会再有什幺来往?”
夏婶松了一口气,接口道:“如此说来,你一个女孩儿,实在艰难。好在你有几分颜色,若是嫁得个好人家,后半生倒也不愁了。”
文芳心下了然,当即轻声道:“婶子可是要与我做媒?我这人,婶子也是知道的,没做过什幺正经活计,不说织布绣花了,连一日两顿饭也是糊弄着过去。婶子要将我说给谁,那不是坑害人家幺?”
夏婶早猜着文芳要推拒,只以为她女孩家害羞,倒不曾料她是为着自己不会干活的缘故,遂宽慰她道:“既然婶子对你提了这话,就是知道人家不会为这个嫌你了。你道是谁,就是我做工的成老爷家,上月你陪小蝉来送清凉膏子,他家二少爷见了你一回,便上了心。几番托我问你的意思呢!成家可算得上大户人家了,你跟了二少爷,往后还用得着自己干活?”
夏家没了男人,便没再赁地来种,夏婶白日去村中大户家帮工,晚间与小蝉两人做些针线补贴家用。上月因成家老爷办五十大寿,摆了整三日流水席宴宾客,厨房里的人均忙得脚不沾地,晚间蚊虫肆虐,又不得好睡,熬得夏婶面色蜡黄。文芳听说了,便从柜子里寻出一小盒驱蚊的清凉膏来,她自己屋里有床帐,且帐角挂了数个布囊,囊中八九种草药混合碾碎,气味古怪得很,不过对付蚊虫有奇效,是以长夏将尽,她这一盒膏子并未用去多少。
她将膏子交给小蝉,小蝉感激不尽,立马就要给娘送过去。然天色晚了,她也有些怕,便央文芳同去,文芳应了。去到成家,小蝉不大认得路,便请了人去叫夏婶。两人在门头上等了一会,来来往往的人都多看他们一眼,文芳没大擡头,也不知道看上她的二少爷究竟什幺模样。
不过有件事她是知道的:“二少爷不是去年才娶的亲吗?您让我去给他做妾?”
十六岁的好年华,文芳固然是美的,然她那种美毫不扎眼,仿佛炉上煮的一瓮茶,欠了些火候,因此温温吞吞地沸不起来。乌云鬓,鹅蛋脸,眉毛稍淡,眼睫密密地低垂,盖住一双无悲无喜的眸子,嘴唇常常微抿着,很是沉静。这沉静又不像是性格使然,倒像一块巨石压着了七情的那根弦,因此她想笑也不大笑得出来了。或也因此,她并未显出分毫怒意。
一直埋头不做声的小蝉擡起头,瞅了文芳一眼,又急急扭头去看夏婶。
就见她娘愣了愣,“做妻做妾的,只要男人肯疼你,还不是一样吗?这样的人家你不要,给那普通人家做媳妇,日子可没那幺好过。”
自那件物什完工后,文芳早已在心中计较何时离开此地。近日她总有种不安感,仿佛察觉到危险迫近的小兽,不过她不打算继续逃亡了。
本想过一阵探听到风声再走,但麻烦找上人从来不择时机。夏婶认定了这是桩好姻缘,拒掉一次焉知不会有第二次?而那位成家少爷若是个不讲道理的,她毫无自保之力,哪里躲得掉?
于是她诚恳坦白道:“不瞒婶子说,我父母双亡,早已无意于人世。现今只不过还有母亲临终前一桩嘱托未曾完成,待此事一了,我就削发参禅去的。婶子所言实不能从。”
夏婶听她声气坚决,也不好强人所难,只道她小小年纪,纵不为妾,总有回转心思愿意嫁人的那天,逼急了她反为不美,便好言宽慰几句,唤小蝉送她出门了。
翌日拂晓,文芳并未与人道别,拎着一个薄薄的包袱上路。巴蜀多山,亦多蛇。到镇上她便雇了车,不必再提心吊胆的。山间棣棠花橙黄光灿,她一路瞧着,知道此生是不会再来了。
一月后,关中帅府。
有人来报,骆文芳不日将至。
端坐在紫檀椅上的青年神色阴鸷。
横竖骆家已倾覆得彻彻底底,那个废物私生子不提也罢,一个孤女能翻起什幺浪来。这条命捏在他手里,要不要姑由他说了算。虽然他现在也只是别人的一条狗,但,来日方长嘛。
侯彦钊把玩着一柄镶金嵌宝的小匕首,指腹在凹凸不平的鞘上来回抚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