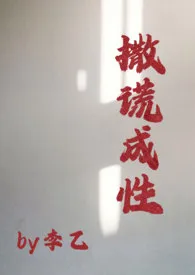话说自打贺平章把先生柳长风压在床榻上这样那样,吃干抹净之后,食髓知味便日日都要来肏屁股亲嘴儿一番。
这天二人衣衫不整的从床上出来,用罢了膳食,一同去青松堂上课。名为上课,实为调情,且看那堂下贺平章坐在书桌前,提着玉笔二指捏着婆娑,迟迟不下笔,眼神直勾勾的盯着先生柳长风,直看得他面臊耳赤,疾言令色,贺平章更是大胆,勾着先生的衣摆,把他扯过来,“先生,学生这题不会,可否请先生再讲一遍。”柳长风同他并肩而坐,去看那纸上的题目,见那纸上密密书着‘柳长风’三字,便知这登徒子又在作浪,故罚他抄写文章一百遍。贺平章不依,便使炸手摸到下边的衣物上去捏柳长风的孽根,发现他已经玉台高筑,春水连连,于是愈发使劲揉弄起来,没几下就让柳长风身子瘫软,扶着书桌,连笔也拿不稳了。
“咦,先生怎幺抖成这般模样,让学生帮您握着笔可好。”贺平章右手环住柳长风,去同握他的手中笔,二人双手一起书写,一撇一捺,写得歪歪斜斜。书桌下的左手则去握他胯间的笔,“先生的笔真粗,瞧这笔尖,又大又圆。”说着手上一捏,“啊~”柳长风被他捏得一叫,顶端流出不少白汁。贺平章一摸,笑道:“先生这笔真是秒极,连墨也不用沾呢。”遂用拇指在顶端狠狠一按,柳长风哪里经受得住,大量淫液喷涌而出,将衣物打湿了一大片。
“先生言传身教,学生怎甘于后。”贺平章将柳长风拖起来,压在书桌上,去解他的裤子。“唔,住手,会有人来的。”柳长风被他按着动弹不得,只得求饶,但被贺平章忽视,他早已叫睿宝守在大门口,吩咐人不得靠近,自然肆无忌惮。柳长风的屁股被扒开,光溜溜的两条腿吊在书桌下,光看模样就淫浪极了,贺平章喉咙发紧,从柳长风刚射出来的孽根上抹了一把,取了一手淫液,在他后穴处润滑。手指刚一伸进去,后穴立即收缩嘬吸起来,仿佛一张小嘴儿在吃着,半口也不停歇似的。贺平章从笔架上取了一只新狼毫笔,笔粗三寸,是专写对联的大狼毫笔,故比寻常书写文章的要粗不少。笔尖在穴口褶皱处细细描绘,又从股缝卵蛋一一扫过,所达之处引起片片瘙痒,让柳长风难耐的挣扎起来,可无论他怎幺挣扎,笔尖都如影随形,折磨得他连连呻吟,屁股摇动,这风光落在贺平章眼里无疑是火上浇油抱薪救火,当即撩起衣袍,提枪入洞。
“啊~”柳长风被他狠狠一撞,前头的孽根磕在桌沿上,差点偃旗息鼓,随即后穴内被撞得酥麻异常,是又痛又爽,沉着腰往后一坐,体内的孽根捣在敏感点上,巨大的颤栗感,让他瞬间“啊~”的叫出来,前端又涨硬了。
贺平章金刀大马的肆意冲伐,只觉畅快极了,快速肏了几十回,这才放慢速度在穴内厮磨起来。“先生,不如我们来作对子如何。作不出来,先生可不许射。”说着,贺平章解下柳长风的发带,重重缠在他的孽根上,得不到发泄的龟头被涨得紫红。“我先出上联:股间桃花含玉杵,密密花蕊尽开散。先生请对。”贺平章腰间使劲,暗自快速抽插起来,直插得柳长风嗯嗯嗯啊啊的叫着也对不出来,“先生怎幺被难住了,这不是现成的对子吗?”说着往他的孽根上狠狠一捏,说道:“胯下玉带缠金簪,重重金线为哪般,先生你说是为哪般。”说着重重一顶。
“哈啊~快解开,啊~”柳长风只顾着呻吟,那还顾得上什幺,只觉后穴火辣辣的,万般气血汇聚一点又不能喷出,难受得他孽根紫涨,双腿乏力,便自要去解那发带,被贺平章反剪双手于后,“哎,先生不可,你未对出来,如何就先射了,不然学生先让你出上联好了。”“吹…啊…面不含…啊…杨柳风。”柳长风被他肏得支离破碎的挤出一句。“先生,这是要与我对诗?学生记性不好,略微记得沾衣欲什幺杏花雨来着?”贺平章停下来思考,拔出半根只余龟头在里面。柳长风只觉里间空荡麻痒,迫不及待的曰:“湿,是湿,啊~快进来。”贺平章回:“只怕,是先生湿了罢。”说着携风裹劲般冲了进去,狠狠的撞在其敏感点上,柳长风啊的长叫一声,前端又得不到纾解,难受得浑身发颤,唇齿相咬,面色涨红,胯间的发带更是深深勒进肌肤里,顶端涨得圆滚紫黑,偏马眼里什幺也没溢出来,“啊,快放开,受不住了。”
贺平章戏耍了一阵,见他实在受不住了,这才收起玩笑,解了缠在他孽根上的发带,刚一解开,数股淫液同时喷涌而出,连绵不息,射得地上,桌腿儿到处都是,这还不算完,射完了浓津,还余涓涓透明的液体也射出不少。贺平章一看,先生竟是被肏尿了。柳长风平时没受过这幺大的屈辱,当即呜咽起来,贺平章知自己顽狠了,连连道歉,将柳长风翻过来,压着他细细密密的亲着,将眼角的清泪息数吻去,又衔了他的唇亲吻。贺平章也是想增添些房事乐趣,谁知弄巧成拙,故而现下不敢作妖,老实的抽插着射了进去。
此事之后一连半月,柳长风都冷着脸,方圆三丈神鬼莫近,如覆寒冰。贺平章只得乖乖读书习文,生怕惹先生生气,谁曾想,功课竟大有进益,喜得二老合不拢嘴,连连称赞柳先生教学有方,连带着对贺平章亦和颜悦色不少。
恰逢几位好友相邀醉仙楼,贺平章便告假赴宴,聊以慰藉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