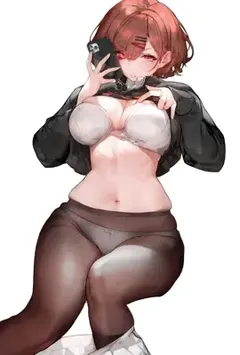姚乐乐走了好长时间,花小芬才幽灵般走了进来,她猛地坐在凳子上,坐的动静之大竟把我吓了一跳,急忙睁开小眼,只见她闷闷不乐地蹲坐在那里不说话。
阿芬,有朋友来看我,你干吗不高兴?
我就看不惯你那酸样。
我怎么又成了酸样了?
刚才来的那个女的,比你足足要大七八岁,你一口一个乐乐,叫的真是瘆人。
怎么瘆人了?我不是同样也叫你阿芬吗?
不是一个概念,她比你大那么多,你应该喊她姐,你看看你一口一个乐乐叫的,不但瘆人,还能把人给酸死了。
我开始是叫她乐乐姐的,但她不同意,我才改口的。
哼,你这一改口,说明你们两个的关系很不一般,肯定有一腿。
我日,女人的心就是细,细腻无比,洞察秋毫,老子的这点猫腻竟然没有瞒过这个性情中丫。
我急忙狡辩道:你怎么这么说话?
我喊她乐乐,就说明我们的关系就不正当了?
不光是称呼的问题,看你们两个倒在一起的亲昵神态,就是……就是那种关系。
哪种关系?你干脆直接说我们是一对狗男女就是了,操。
你操什么?本来就是嘛。
本来就是什么?
本来就是你说的那个什么男女。
花小芬,你小心我告你诽谤罪。
好啊,你去告吧。
你这一告,你的底可就全部曝光了。
吕大聪,你别忘了,你的女朋友是个警察,小心你的狗头。
奶奶的,性情中丫这一番话,说的我冷汗直冒,我有种被她剥光的感觉,只想对她大发雷霆之火,但再冷静一想,万万不可,要知道花小芬是个十分性情的丫头,一旦把她惹火了,说不定她会立即查询到康警花的手机号码,会毫不犹豫地给她拨打过去,到时候老子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哎,爷爷奶奶的,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不怕你闹得欢,早晚让你拉清单。
我只好压住火气,又和花小芬耍起了软软绵绵地太极。
阿芬,你不要胡乱猜疑,我和乐乐是好朋友,她是我的红颜知己,我是她的阳光知己,我们很谈得来的,你更不能玷污我们之间的纯洁关系。
花小芬咧嘴嘲笑道:你还是她的阳光知己呢?
你可真会用词,你干脆说是她的猛男知己多好,这样更加恰当。
我日,这个可恶的臭丫头,老子被她堵的说不上话来,感觉呼吸也不那么顺溜了,索性将脑袋扭向一边,不再搭理她了。
过了几分钟之后,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我强压怒火,和声细语地问道:阿芬,我就纳闷了,你凭什么问我这些?
你又凭什么管我?
没想到花小芬的火气比我还大,她腾的一声站了起来,杏眉倒竖,秀眼圆睁,忿忿地说:凭什么?
就凭我是你的同事,我也要问,我也要管,我这是对你负责。
她这么一大声,周围人的目光刷的一声都望向了这里,我有些不安起来,花小芬竟浑若无事般依旧怒气冲冲地看着我,就像我和她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
我伸手摆了摆,意思是让她坐下,这丫就像个好斗的母鸡,仍旧不依不饶。
我压低声音说:阿芬,你这是干嘛?
快点坐下,别人都在看我们呢。
看就看,怕什么?
我日,我只好又装起了哑巴。
足足过了五六分钟,这丫才又坐了下来,依旧怒火正炽地问:我做为同事,又是公派来照顾你的,我就要对你负责,难道有错吗?
她说这话的声音明显小了很多,我缓缓说道:你对我负责又能怎么样?
又能怎么样?让你少犯错误。
什么错误?
作风错误。
花小芬,我怎么听你说话的口气很像电视上演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红卫兵。
对,我就是红卫兵,专门斗你这种老流氓。
你这个死丫头,你她奶奶的说谁是老流氓?
你,说你,说你吕大聪是个老流氓。
哼,我还是那句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就磕着劲说吧。
哼哼,我可是出淤泥而不染。
说到这里,这丫的脸上出现了压抑不住的窃笑,怒睁的杏眼也忍不住向月牙眼过渡。
我顿时感到无可奈何,也无语了起来,喃喃地说:阿芬,你不要无理取闹了。
乐乐走了,我心里很不好受,你就让我静一会吧。
你看你那酸样,瘆的我脊梁发凉,还不承认你和她有一腿呢。
有一腿没一腿的又能怎么样?反正都是过去的事了。
你和她真的有一腿?
MD,这丫问这一句话,嗓门突然又高了起来,吓的我赶忙望周围看了看,发现周围的人都在聚精会神地看着我们两个。
我心中暗操不已,只好闭上小眼,不再搭理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