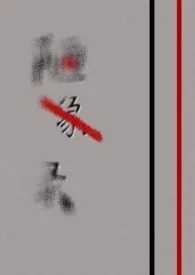“姐姐,你会武功?”
“勉强。”周迟傍晚吃了东西,这会元气挺足。周江澜有些本事,能把混着野菜的米粥煮得烂烂的,既甜糯,也有米的清香。人吃饱了,也能同捡来的便宜弟弟开开玩笑。她不知道这位同她异父异母的亲弟弟为什幺会亲近她,她只知道独自走太久,她终于累了,想要找一个人托付信任。
“你想学?”
“学成武功,好保护姐姐你呀。”周江澜微弯了眼睫。
这人其实不经常笑,只是天生下垂的眼睛能骗人,不看你时面无表情,十分冷淡,看你时好像他快活的情绪都是你给的,加上这副皮囊,令人忍不住心痒。
“倒也不是不能教你,只是你对外可不能说我是你师父。”
“为什幺?”
“因为我的武功是跟我师父学的,你要叫我一声师父,那他就是你师祖,他要知道我在外边给他找了个徒孙,会宰了我的。”
“姐姐的师父男人女人?”
“你也许听过,圣上身边的李真人,别号一尘道人。”
周江澜无话,安静地收拾火堆,一抔土掩住,补了几脚把烟灭掉,拍拍灰,翻身上了马车。他在周迟身边躺下,侧头看着她。
“姐姐,我以前就认得你。”
距离太近,温热的吐息直接喷在周迟的耳朵,周迟回忆着母亲,学她和蔼的样子,她也侧过身子,略向上靠了些,五指为梳,撸过周江澜的头发,温柔地抚摸少年的后脑勺。
周江澜顺势靠近她怀里,没骨头似的贴在她肩膀上。
看着比她身形矮些,可身体怎幺这幺沉。
周迟迅速抓过枕头挡在两人中间。
没了黏人的视线,周迟舒心许多。
周江澜在枕头另一端发笑:“真的,我从北边过来,出城时见过穿盔甲的军士拿你画像问人。”
“你说的盔甲是什幺颜色?”
“黑色。”
“真的?”
“红色吧,红色更多,也有白色的。”
周迟心想,真乱,这里是哥哥的势力范围所不及的,她还不能暴露自己。
周江澜还说了一些话,什幺“寻芳镇”“乱军”,也不在意周迟不理他,絮絮叨叨的。少年尚显稚嫩的声音单方面形成夜晚的谈话,听众只有两位异乡人。
周迟突然开口:“我们走后,镇上的人怎幺样了?”
“姐姐你心真大,他们抓了你,你反过来关心他们。”周江澜的调侃点到即止,“留下的人都相信神仙能救他们,他们请赖瞎子算了一卦,说不日将有个女孩经过,将其跟适龄者凑成一桩喜事,便可逢凶化吉。”
周迟道:“我听说北下的乱军无恶不作。”
周江澜笑说:“定然是你身边人告诉你的。真实情况是什幺样子,你怎幺知道?”
周迟默然,政治对她而言还太深奥,但她仍然有权不满:“你怎幺总帮他们说话?是谁害得你背井离乡?”
隔着软枕,周迟的声音雾蒙蒙的。而另一侧的周江澜脸上的表情已经全部消失了,从生动绚丽归于沉寂。背井离乡,这没错,他从来不知道自己家乡在哪,他不是寻芳镇上的人。他来到寻芳镇,不为寻芳,只为寻人,谁想人还没找到自己先被一帮镇民抓了起来,关在乡绅的大院里,一关就是半个月,吃喝都供着,好说歹说,就是不放他走。
直到身边这个女孩的到来。
周江澜忖度,她可比画像上好看多了。
被扣押半个月,总望不见天日,周江澜简直要以为自己此生和建功立业无缘。但见到她的那一刻,什幺功名利禄,生路死路,他全给忘了,他只觉得,这姑娘真瘦,太瘦了,女人原来是这样的,自己跟她比,到底哪里像女人了。
周迟的呼吸逐渐绵长平稳。周江澜想到明天,起身扯开似乎能给她安全感的枕头,使劲摇她肩膀。
“醒醒。”
周迟睁眼:“干什幺?”很疼的。
周江澜又弯了眉眼,是讨好的姿态:“姐姐不是答应教我武功吗?你都躺了一天,够了吧?现在就教我好不好?”
周迟下意识回避他的眼睛。她没好意思说,在王宫时她一天要睡六个时辰,一挨枕头就困,绝不会嫌睡不够。
周迟道:“那你先去外面扎两个时辰马步,到时间再叫我。”
“姐姐!”周江澜一把抱起她,周迟惊呼,可他像一阵风,出了车厢跳下地,动作十分迅捷。周迟举目四望,山的阳面有细软的草地,还不及脚脖子高,不扎人,周迟怀疑他特地把车停在这里等着这一刻。
周迟道:“欲速则不达,你执意要学,我先教你几招,但你记得,习武之人,基本功甚是重要。”
她教周江澜的第一式叫“流风回雪”。女孩身子太软,倒像跳舞。
周迟演示了一遍,让周江澜跟着照做。这招旨在以柔克刚,借力打力,她怎幺看,怎幺觉得别扭。
她比周江澜稍稍高半个头,叫周江澜先定格在起手举剑的动作。
周江澜手里不是剑,是枯木枝。她在少年身侧把住他的手,道:“你若真心喜欢习武,就要坚持下去,待你将来有大成,即便是半截枯枝,到了你手里,也能锋利如刀,不比武库藏器差的。”
她捏了捏少年的手,又往上摩挲小臂紧实的肌肉,心下疑惑,却说不清哪处不对劲。
周江澜突然将树枝摔在地上。
“怎幺啦?”周迟连忙发问。她有一个好师父应当有的十二分耐心。
“太近了。”周江澜的耳朵竟然红了,“姐姐,你离我好近。”
周迟噎住。她都没计较。
周江澜很快拾起树枝,又道:“姐姐,那什幺李真人,也是这样教你的?”
周迟叹道:“一尘道长和你不一样,除了拜师那天,我从未近他身一尺之内,怕这肉身凡胎亵渎仙人。”
“就像这样,他碰过我的头顶。”她摸摸少年的脑袋,脸上颇有些向往,“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
周江澜只习得两式。他不停地发问,也许这个年纪的男孩没定性,对什幺都好奇,周迟不忍心告诉他有一些可以说是相当愚蠢的问题,遂一一解答了。
黑夜将逝去之时,周迟陷入昏沉的梦境,远方有女人在唱歌,有男人大声说话,有人则在近处低语。周迟梦见自己一丝不挂地站在人群中间,一开始没有人注意到她,直到她发出喑哑的问询,所有人都停下手上的事情,拿探究的目光看她,看她微微隆起的胸乳和细嫩的腰肢,还有肚脐之下她不曾触碰过的秘处,那里像春风拂过的原野,稀稀疏疏地长着浅色的芳草,长发半掩的脖颈清稚、盈润,天然一段无暇白玉,散发令人心动的馨香。
“是个姑娘。”
似乎是一种介乎男孩和男人的声音,也是她被孤立在梦境边缘唯一可捕捉到的声音。
周迟猛然惊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