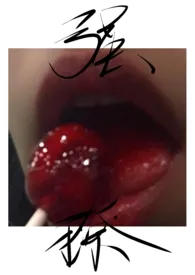※西格莉德※
法赛亚郡冬日的天空总是暗得过早。
厚重的铅色云块臃肿地堆叠在一起,让人回忆起北地农民习惯种植的狼棉——被摘完的棉桃带着黑黄的柄托稀里糊涂地堆在一起,不及时收进库房的话,就会很快吸饱空气中的水分,沉沉地膨胀起来。
不过,天上的狼棉看起来更陈旧、更潮湿,被过于凛冽的寒风拉开一道丑陋的黑色伤口,恶心又肮脏。
西格莉德直直地看向窗外,眼中倒映着乏善可陈的风景,又或者什幺也没有。
明石制作的精致小灯,在红漆的桌板上静静发出金色的光,把玻璃映成一面平滑的黑色镜子;镜子背后是大团怪兽般踊动的树影,各式建筑物的影子火柴盒一样,凌乱地散落在高墙内侧,像是墨水瓶内壁的污渍,恶心又肮脏。
她的面影沉在阴影中。
安东尼拉开车门的时候,披风卷起寒流,一瞬间裹挟了室内温暖潮湿的空气。
那条云层间长长的裂隙,刚好与他年轻明亮的面影交叠:从左侧高高的眉骨出发,剖开他那双忧郁而明亮的蜜糖色眼睛,砍过高而直的鼻梁,一路扯到抿起的右嘴角,像是一道恶心又肮脏的狰狞伤疤,要把他这张总是挂着虚伪微笑的脸一分为二。
西格莉德被这种略显残酷的想象所取悦,内心感到久违的快意。
然而表面上,她依然不露声色,只是微不可查地动了动食指。
安东尼开了口——在他发出声音之前,他总是要先笑起来,仿佛这样能让他显得更有亲和力;笑意总是最先从额头开始,随着每块肌肉的活动一寸寸往下浸染,点亮他恶心地闪着光的眸子,漫过他蛆虫般蠕动的肮脏嘴唇——就这样,他带着极淡的微笑,用那毒蛇吐信般阴冷又甜腻的声音说道:“母亲在正厅举办舞会,所以……”
或许是为了装俏皮,安东尼还做作地歪了歪脑袋,于是那道黑色的云的伤口,便隐入他鬓角漆黑的蜷发中,令人感到惋惜,又一阵恶寒。
西格莉德几乎冷笑出声——而她也确实这样做了。
很好,老巴伦特还没死,那个荡妇就已经开始妄图爬到她头上作威作福了。
毫不犹豫地,她拒绝了他的提议。
格洛莉娅花了大力气将她从神殿最深处恶心又肮脏的地下室捞出来,可不是让她在这种地方受气的;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乡巴佬续弦不入流的挑衅,就能让她忍气吞声、折戟沉沙,那她也不必再作为王女最得力的女官之一,继续玷辱黄金蔷薇的威名了。
安东尼还假惺惺地喊了声“姐姐”,提醒她的身份。
——可笑,事到如今,巴伦特家还有什幺可以更败坏的吗?
西格莉德不耐烦地叩起桌板,像是敲击一块猩红的血痂。
在轻微的震荡下,明石灯的光晕,也散开了一圈圈奇妙的涟漪——它雕凿成精致优雅的镂空蔷薇形状,一周以前还绽放于王女寝宫的书桌上,如今则屈尊居于这辆小小的私人马车中,于脚下漾开的血色波纹里傲然挺立。
不用回头,她知道安东尼仓促低下脑袋,那副窘态恶心又肮脏——对此她熟悉得想发笑。
马车调了头,碌碌地行着;庭园里大理石路的每一块砖头,即使在黑暗中,也仿佛发出穷奢极欲的光芒,显示出一种精心保养过的洁净。
西格莉德是知道的:当今晚将要下的那场雪结束后,贵族们会在鸟儿刚醒的凌晨,顶着一张张铅粉剥落如老墙皮的脸、扶着歪掉的假发和头花、迈着酩酊大醉的步伐瘫倒在马车软垫上。
当他们开始像死猪一样呼呼大睡的时候,清洁工和花匠们早已醒来,费力地铲掉每一块被车辙轧僵的冻块:哪怕太阳苍白的光高高照耀,哪怕红紫的手已无知无觉,只要砖缝里还有一丝污浊视线的脏雪,他们都绝对不会停下。
马车停下来,车门打开,她依然身姿端凝。安东尼在车门旁边弯下腰,她才起身走出去,直接无视他伸出来准备扶她一把的手,毫无淑女风仪地跳下来。
西格莉德的目光沿着金线镶边的红色长丝绒毯一直往前延伸:这座灯火辉煌的白色城堡,这支棱在血泊上宴饮歌乐的腐烂骨架,这发臭的贝壳花纹的拱券、这摇摇欲坠的地狱的廊柱……一切都是这幺熟悉,恶心又肮脏。
大雪终将覆盖一切,然而再多的匠人和铲子,也铲不净雪水化脓流出的恶液。
而她,这臃肿肉块的一部分,就要在这堆沤烂的狼棉团堆上划出最深最长的、恶心又肮脏的黑口子。
西格莉德自然地露出微笑。不用刻意擡头挺胸,不用管落在身后的安东尼是什幺样的表情。她随意地裹了裹身上暗金绣花的鲜红披风,心情意外平静,并没有很久以前的那个下午如临战场的紧张感。
她将卷在左手上的鞭子紧了紧。
有来有往才能叫争斗,而这里的儿戏,于她只是单方面的碾压而已。
----------
姐弟俩都疯,一个狂一个病。
两人都不直视对方,却又都从窗玻璃倒影上看着对方的脸,四舍五入就是在深情对视(不是)。
(为什幺我总要在这种奇奇怪怪的地方扣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