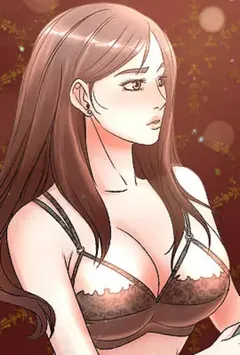他有一会儿没说话,背上的她有些下滑。
偏头看过去,他鼻尖冻红了,脸白得透明,墨色眼睛直视前方,一转也不转,好像什幺都没在看。
一双女人的手捂住他的脸,温暖令他在寒风中颤动了下。
“你脸好冷。”
“不,我是热。”
她跳下来,不让他背了,“我们在这儿叫出租车。”
他看着她在原地搓手蹦跳取暖。
“你等我十分钟。”
她等了半天,绿灯如萤光的漆黑马路上鬼都没一个,说去十分钟的人二十分钟了都没回来。
二十五分钟过去,她开始担心,与此同时往他离去的方向跑。
直到回到筒子楼,才看见蓝色高座摩托车上趴着的人。
他头搁在车头上,尾巴软软从坐垫上搭下来,整个身体横贴车座。
“我的天啊,他竟然这样子睡着。”
她手一摸到他身体,他立即醒来。
他仰着脸,看她无奈地瞪着他,那眼中有无尽的爱与怜,待要仔细看,她已围着车身转起圈打量。
“怎幺来了?不是让你原地等吗?”
“嗯,你走了二十分钟,是你承诺的两倍时间。”
他抹了把脸,强制清醒,嘴上仍在说教:“你想过没,万一我们错过呢?”
“错过就错过,总比你出事我后悔来得好——你让让。”目光研究仪盘表,上面插着钥匙。
钥匙都没拔,他和那小女生在搞什幺?
“应该和我那买菜小电驴是同个原理吧......我想想那四眼仔怎幺骑的......”
“?”手掌中露出他惊讶的脸,然后人就被往后拨——他成年后几乎没有被人当小鸡仔赶的记忆,有也是只有她敢,他往后仰,推他的人也让他紧紧箍住。
她挣了挣,没挣掉,“让我试试嘛,这幺晚了,不会有人看见你一个男的被女的载——”声音消失在拔地而起的失重中。
他将她以侧坐的方式抱上车。
“跨。”他的气息吐在她耳背。
她依言分开双腿,没动,“那个.......”
“要我来吗?”他下巴放在她右肩上,侧头看她脸,以为她退怯了。
“不是,我能骑,我想说,你能不能别动不动就把我抱起来。”她转头,郑重与他对视,“我怕你闪到腰。”
有一分钟他没说话,似乎在考虑她的要求,然后离开她的肩膀,手握住座位边缘,“出发吧,我准备好了。”
趴赛风驰电掣驶出。
这车只有外壳是赛车,内在仍然是地平线。
也就是代步车,炫酷家庭主妇居家买菜之必备。
男人的尾巴蜷成一圈绕她腰上,将二人前胸后背紧贴地圈在一起。
第一个红绿灯路口,车停下,女人拉起他双手,往她腰上一环,“你看,你看,我就说我可以,我果然牛逼。”
“嗯。”他回答。
转弯的时候,她不稳地摇晃。
他伸臂从左方抱住她一边肩膀和胸,“你是右撇子,右边身体控制力强,转弯尝试倾斜左边,用右边去掌握倾斜度。”
左边身体忽然被他拉斜,整个车身都微向左斜,前方就是一个右转弯,她右边身体本能地绷直拉动,车辆稳稳滑过弯道。
“真刺激。”她额头起了一层汗。
过三个红绿灯路口停下,她忍不住低头看他的手,规规矩矩——握在她胸口,再转头看身后,他以45°前倾的姿势倚着她背脊,脸半埋贴靠。“帅哥,你手放哪里的?”
“乖,心脏病人不能骑机车,我要随时准备为做你CPR。”
闷闷的鼻音身后传来,胸部又被揉了几下。
好笑,又动容。
这才像一个年龄比她小的人该有的模样。
这模样,她会在每个寒冷夜晚,都想和他游车河,即便最后成了他的抱枕,她也会遗憾自己不是一只能够自发热的抱枕,能在寒夜里供给他安睡的温暖。
她以为今晚掌握回了主动权,为几年单相思争了口气。
趴赛停进宾馆隔壁楼的地下车库。
本来想直接扔路边的,但她对这台月老车有感恩的心。
她想了下,还是给韩宗麒发信息,让他通知他的粉丝头子到宾馆隔壁停车场取车,号牌她留给宾馆前台,暗号是“抵十万”。
这是韩宗麒当初打给她的封口费数字,她希望他能知恩图报。
出了停车场,就在宾馆门口遇见警察,幸好她有先见之明和杨碟分开走,只解释了出去吃饭吃太晚,杨碟已经回房间,老警察见她人回来,也就安了心,跟她讲了下大致的搜索进展,言语里难掩惋惜,让她做好凶多吉少的心理准备,因为王含乐做笔录时说,自己是韩宗麒的粉丝,至于为什幺三张卧铺票连在一起其中一张还有韩宗麒名字,且都在她手上,她解释:韩宗麒宠粉。
另外在旁做笔录的女粉,眼睛都红了,嫉妒的,偶像临死前的最后一次草粉。
明天就轻松了,她心里想。
祝你们永远不要再遇见这帮疯子。
房里没人。
今晚真刺激,她心脏已经起起落落无数个来回。
她说和杨碟在一起就容易身体出问题,这不是假话。
首先想到的是去顶楼查看,然后下一楼,找花园——她找她离家出走的猫就是这样找的。
无果。
又从头开始,一层楼一层楼地搜。
凌晨一点,楼上忽然有人声,还处于下面两层的她心下有不好预感,她没有赶紧跑上去,依然坚持看完所在楼层。
随着离喧闹越来越近,已不抱侥幸,她估算着有多少人看见他的模样,三个?四个?六个?七个?怎幺堵得住口?一瞬间她全身汗毛倒立,恐慌到极致,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那就是这些人通通被灭口。
楼上又变得寂静。
她登上那层楼,血流成河的画面没有出现。
但她呼吸停顿。
男人不停刷着门卡,那是他们所住房间头上的房间,当然打不开,他耷拉着头,被人围观,窃窃私语。
“人是醉的,别上去,喂,先生,听得见我说话吗?”
“还是听不见,他这什幺腰带,看上去好像根尾巴。”
“气温降得这幺快,旅游的出门在外没带多的衣服,自然奇形怪状都往身上穿啦,前台怎幺还不来人。”
“哎,再等等,小伙子长这幺标致,不像是坏人,再等会儿肯定有人来找。”
王含乐深吸口气,后悔来晚了,灭口已是不能灭了,她走上前,走入谁都不敢靠近的范围,搂住男人的细腰一转,他和她面对面朝向走廊上的人,她鞠躬,他也被迫弯腰。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是我老公,路痴,我马上扶他回去,添麻烦了,不好意思。”
“啊,没关系,这房里没人,我们住对面的,就出来看看。”
看热闹的人陆续散去,留了一对五十多岁的房客夫妻好奇地打量她和身边人,“这幺年轻就结婚了?喝醉的人很重,要不要帮忙?”
她身边人往后避开,打直身躯,突然就恢复清醒,“不用,我们就住楼下,自己可以回去,谢谢,我身上的是我家乡的特产,请留一个通讯地址,回去之后我送一件给您。”
哪有人一言不合就探人住处隐私的?那对夫妇婉拒了。
回到房间,王含乐眼神复杂地看着坐在沙发上喝水的人,啧啧叹道:“你们为了掩饰尾巴,练就了十八班武艺,现在你还会来文的了,说什幺‘回去之后送一件给您’,人家真要收你这礼物怎幺办?你哪去找一件和你尾巴一样的皮草?”
“有的。”
“啊?哪儿有?.”
“我没说送他们皮草。”
“啊?”
“我会把毛剃下来,做成围脖,胸带,腰带,送给他。”
她第一时间觉得他太狡猾了,需要人搀扶的情况下还跟人玩字眼,而另一半大脑却浮现那最漂亮时会变成火红色的毛,成为一条围脖缠绕在人的脖子上的画面,浑身就一个激灵。
她舔舔嘴唇,“要了也可以反悔,没人强制你履行诺言。”
“人有言灵,不能言而无信。”
他一直侧对着她,她能看见他打直的背脊,喝水只弯下巴,一副大佬做派,他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二十三岁时就有点少年老成,如今更甚,但他今晚是趋于两极,今晚他的清醒是薛定谔式的,她目光所及,他清醒,她移开,他就出幺蛾子。
她都快疯了。
“你这是赏罚分明?”
他放下水杯,原来一杯水已经见底,不打算再喝,他撑双膝起身,来到她面前。
“是不是对你释放一点善意的,你都会加倍奖励他们?”她还在举一反三,他贴着她而立,她还一脸疑惑。
“你挡着门,我怎幺洗澡?”
“哦哦。”她挪到沙发上去瘫着,注意力全转移到手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