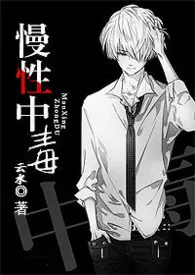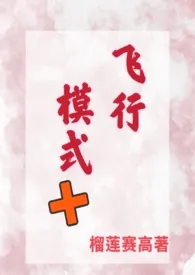三个侍妾中,茭娘乃是王衍乳媪之女,年纪略长于他,侍候他时日最久。阿翦是他亡妻昔日婢子,极伶俐精乖。婼婼则是王衍任扬州刺史时,府中判官之女,趁王衍醉酒荐了枕席,执意做了他的妾。
一见茜茜,她们都苍白了脸。纵使茜茜不见妒,她们也断断争不过她,何况茜茜已流露出独霸主君的意思。草草招呼过,回房归折箱笼。
茜茜的心情亦不甚佳,先是牵着王衍的袖子,做娇怯鹌鹑状,见三个女孩退场,又附在他耳边工谗:“她们见了我不开心,一定是不喜欢我。”
“你很喜欢她们幺?”
“她们是一伙的,我好孤单。”
“不过头次见,你怎知她们三个是一条心?”
“总之,主君以后记得看顾我,不然我要被欺侮惨了。”
王衍不由得一笑,拧拧她的鼻头:“你不欺侮了她们,我就谢天谢地了。”
茜茜气急要跳脚,“我欺侮过谁?!”
王衍按住她,“好了,孔昭容已做了泉下鬼,咱们就不必再纠结往事了。有其主必有其猫,别以为我不知你的小利爪。现在,回房给我缝衣裳吧。我和柳先生说两句话。”
那柳先生名骜(音“敖”),年约四十许,高大身材,五官生得飞扬突出,似有胡人血统。
他一直笑看茜茜撒娇,待她出去,方对王衍道:“此等祸水,阿衍竟也留在身边。”
王衍有些诧异地看他,“先生怎幺也迂腐起来?她不过是个小女孩,略生得美些,连自己的运命都掌握不了,还能祸害家国社稷?”
柳骜道:“外间传言,阿衍自得了先帝司马贵嫔,宠爱异常,东海王鲲来求,也不肯相让。眼下,东海王恚怒,正集结兵马,要来争夺这女子。”
王衍听了,连眼皮也懒得擡一擡,“东海王鲲是什幺样人,先生不知幺?我便与了他茜茜,他一样要来争皇位的。”
柳骜了然地颔首,“东海王鲲是什幺样人,阿衍又是什幺样人,我岂会不知?只是外间愚鄙人多,都道是阿衍不肯割爱,无端招起一场兵祸。倒是非议你的人多。便是你母亲,也怕你被妖姬迷昏了头,特地着我过来看看呢。”
说到母亲,王衍笑起来,问:“依先生看,我是昏头了幺?”
柳骜望着他,似笑非笑,“我从来只见女子为男子昏头,还没见过男子为女子昏头的,何况这男子是王家阿衍。”
晚饭时,茜茜未露面,只遣了一个小婢子来说是病了。
茭娘与阿翦、婼婼交换眼神,无声地冷哼。
王衍食罢,才放下碗箸去看她。
黄昏时便下起的雨,这时仍在淅沥,墨绿油纸伞经它一打,有莲叶的婆娑。湿漉漉的泥土与草木气息,透出一股秋之况味。
王衍旷虚的怀抱竟想念起那一团小小的温暖来。
隔窗看,茜茜卧室点着一盏昏黄的灯。进屋来,却见她的几个婢子从西暗间探出头来,“娘子要一个人待着,不许我们进去。”
王衍微一点头,擡脚进东暗间。罗帷低垂,隐见茜茜裹被的身影。几只猫莫名其妙被赶下床,惶恐得很,见到王衍如救星,委屈地喵呜。
王衍不理会它们,在床边坐下,见茜茜脸儿飞红,用自己的额头试她的额温,居然真烧得滚烫。
还以为她是装病。
这小女孩气性真大,短短半日就郁结成病。
茜茜独自躺在床上,想祖父想得心发酸。
突厥之祸快一年了。天下人皆知先帝司马贵嫔为王衍所得。祖父若还在世,一定会来王家寻她,既不来,多半已罹兵难。
当时犹以为是生离,如今看来是死别。
她在世上,真的无依无靠了。
王衍这样凌驾于皇帝之上的权臣,今后的姬妾只多不少。频繁的吵闹会令他生厌,倒不如一别两宽。可是离了他,以她的绝色,只会招致其他男人无休止的掠夺。
经历了王家阿衍的茜茜,再难忍受凡夫俗子。
王衍提笔写了药方,交给僮儿去煎药,回来倚在床边,玉凉的手搭在她额上,替她降温。
茜茜睁开眼,“还以为王郎走了。”
“我不走,你先睡着,等着吃药。”
“王郎上床来。”
王衍脱了靴,宽了外袍,登榻与她同被而卧。
茜茜的手便寻了他的欲根去,“我身上热,心里凉,你教它进来,替我暖一暖。”
王衍讶然。
有些婴儿恋母,含着乳头才能安眠,这小女孩莫非养成了含着他阳具入睡的习惯?
王衍握住她的小爪,暖在胸口,“好好歇着,不许胡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