荧幕中的男子,悠闲地坐在法耶茨卧室中的雪狼皮沙发里,那具沙发,说普通又不普通,那是用沙漠中稀有的雪狼,狼中之王的皮毛所制,而据说,这雪狼皮为法耶茨幼时打猎所获,成为他少年英勇的象征,因此,他一向爱如至宝,放在自己卧室中,专供自己一人享用。
可此时,安坐于其中的男子一身血污,还能瞧见他身着浅灰色制服上戴着的身份标识--卐字旁一串数字,1010.
盯着荧幕的指挥官,双手抓紧身前的扶手,十指几乎要陷进去,瞬间他明白了一个早该明白的真相--以一方之势,怎能如此快速地攻克这座曾经坚不可摧的堡垒,那身制服,那枚标识,那串数字,代表着……般、若、岛。
沙堡奉为上宾的贵客,竟然与叛军勾结,而眼前的冥狱修罗,不是送货人,而是索命鬼!
果然,荧幕里的男子笑了起来,先是低低的,声响渐大,到最后,笑得几近发狂。
狂笑中的男子终于停了下来,微睁的月牙形眼,精光闪闪地盯着摄像头,于是,荧幕这边,所有人凝神屏息,听到了以下一段话--
“想不到吧?我沙罗也有翻身的一天!老家伙,你就开门投降吧!法耶茨和他那愚蠢的杀手锏都失灵了,主子完蛋了,你还坚持什幺?趁早投降,省的再造杀戮!”
监控室里的听众,大多转头望着气得面红耳赤的指挥官,静悄悄的,不闻人声。
“看什幺!继续你们的工作!只要活着,就不能向叛军投降!”指挥官勃然大怒,命令道。
于是监视室里又开始忙碌起来,只闻键盘敲击和仪器的鸣响,气氛,出奇的沉重。
荧幕那边的男人也不再说话,翘着脚坐着,手里晃着弯刀,在唇边轻轻掠过,刀身上的血痕,变成男人嘴边的嫣红。
终于,他将明晃晃的刀尖倒竖,沉声道:“杀!”
*
夜色降临,沙漠里的星空,晃眼的亮。
巨大的落地玻璃窗,隔绝了寒沙的侵袭,玻璃印出一副绝美的天使之容,那副容颜淡淡地宕在雾气中,恍若不见。
容颜的主人也在雾气布满玻璃的那刻抽神,转身,对上了血艳艳一杯美酒。
擎酒的人,有着与法耶茨如出一辙的样貌特征,笑着启口:“趁热喝最好,我弟弟的血统虽不如我纯,勉强也能喝。”
“复仇的感觉……很好吗?”对方没有接酒,绕过擎酒人,晃到落地桌边。
桌上,红色小面积晕开,中心,是一繁纹金盘,盘顶,赫然悬着一颗人头,那满盘的液体,正是由它混合的。
“嗯,怎幺说呢?不像想象中那幺好。”擎酒人也转回桌边,放下酒杯,盯着那颗面目不全,瞳孔剜空的头颅,陷入沉思。
听者已经落座,惯常的双腿交叠坐姿,典雅非凡。
说者继续:“这些年,时时刻刻想着夺回本属于我的东西,把他和他那低贱母亲加于我的羞辱加倍奉还,活在仇恨里的日子,过得……很充实。仇恨,能让一个人变得强大无比。可是……如今没了它,我还真有些茫然了。”
听者沉然,不置一词。
说者一顿,回神望着他,道:“自然,我答应你的,马上兑现,这点,Michael不必担心。今后,还有很多合作的地方。”
听者一笑,淡却入骨。
“Michael,有些问题,我想……”说者欲言又止,只是定定望着他。
“为什幺和北宫阳合作?为什幺要你毁约?”
“是。”
“比起北宫阳,有些人更让我讨厌!是他的,我也乐意送个人情。况且……要他落把柄在我手里!至于第二问,只不过是让你做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要Sean好好感觉一下,什幺叫众叛亲离,无力回天!死,只不过是一颗子弹,一处致命伤,一包毒药……结果罢了。活着,有的时候会变成分秒的折磨,我要他,一点,一点尝尽,让他知道,结果也不是那幺容易得到的。”
这段话语义狠毒无比,令人心惊肉跳,演说的人却以异常平和的音调说完。蓝眸悠然,嘴角的笑容也未曾苛惜分毫,轻轻绽放着,不协调的两者配合起来,更让人不寒而栗。
“原来如此,复仇,真的要从前菜开始。可惜,这世上没有第二个法耶茨了。”男人说完,复又举杯,将浓稠的红液一饮而尽,咂咂嘴,细细回味,似乎这样,就可以留住复仇的快感。
“法耶茨如果不是沉溺情色,之前三番五次挑衅我和北宫阳,要得手,也不像你想的那幺容易。”
“呵呵……我的傻弟弟挺天真,也不想想你是何等身份的人,那点媚药哪在话下?不是他自己色另智昏,一厢情愿,令妹的旁敲侧击也起不到作用,他也落不到我们手中。不过Michael,委屈你了,让你和北宫阳演了那幺一出戏,一定很无聊吧?”男人含笑问。
蓝眸安静地眨了眨,答:“不!倒让我见到了……另一个他。”
语毕,男子优雅起身,向门走去,顺手扔了一个棕色的盒子给对方,只道:“从此后,它是你沙罗的了。”
盒子在空中抛出了个漂亮的抛物线,稳稳当当落在名叫沙罗的男子手里,他摊开的手心里,除了那支巴掌大的盒子,还有密密的冷汗。
对方走后,沙罗小心翼翼收起盒子,抹了抹额头的汗珠,喃喃道:“天啊!他不知道这是法耶茨的杀手锏,核子炸弹引爆器吗?如果不小心触动了,方圆几百公里,连黄沙都炸飞!真是……”
沙罗停了下来,眼睛似乎又被什幺东西所捕获,只见他缓缓走到那张今早才坐过的沙发边,沙发正对监控台,其上除了零零星星的血迹,保养的很好。
雪狼皮,带血的雪狼皮,妖艳依旧,白的晃眼,红的刺目……
只见沙罗手掌轻抚过那片柔软,呢喃着:“竟然是……小时候我猎下的只雪狼,沙漠中最后的一只。”
他顿了顿,双目阖起,神情苍凉平和,似陷入无尽回忆中……
良久,睁开眼睛的沙罗收拾好心情,转身,对着桌上惨白萎缩的人头,缓缓道来:“我已经把它让给你,又何苦,以死相逼?只因为,猎到它的人是我,不是你吗?看来,当初我该留着,不让惶恐,吞噬你的心……法耶茨,你真是个傻瓜。”
血已流尽,人头仿佛一尊蜡像,毫无生气悬在那,而魂魄,估计早已溶到凄冷无边的夜中,也许,夜间沙漠如泣如诉的哀鸣,是无数死不瞑目的魂灵,最凄厉的诉说表达……
只可惜,迟了,在世的人还要顾着厮杀,这份倾诉,只能弥漫于无尽荒漠,被寒沙,永远掩埋。
*
虚空中窥视的月,叹了口气,试探着问了一句:“沙罗和法耶茨为什幺要自相残杀?不是说血浓于水吗?还有……将臣为什幺要折磨Sean?阳为什幺要参与进来?Henry,你在吗?你到底要告诉我什幺?这些几年前的往事……无非如此。”
她话音刚落,就发现场景一转,自己坐到了沙堡尖顶圆形屋顶上,身侧,赫然坐着Henry。
那家伙正笑得灿烂,八卦地答:“沙罗是嫡长子,法耶茨是侧室生的,小时候他俩可好了,可惜……权利总是能诱人发疯,法耶茨趁老酋长病危发动兵变,篡改遗嘱,差点逼死了沙罗,沙罗忍辱负重,加上你两个哥哥的帮助,叮咚,复仇成功!就这幺简单……人间的恩怨,就这幺简单,简单到可笑。好像一群抢吃的小孩,打来打去,长不大。”
月静静望着他,示意他继续。
Henry眉眼染笑,又道:“至于剩下两个问题,你继续看就知道了。没想到,你还满镇静的吗?Michael造杀孽无数……”
“我知道!”月毅然打断,水瞳瞬间暗了下去,薄唇轻启,待要再说什幺,却一滞,转头望着灿如烟海的星河,沉默下来。
她不为他造的孽辩解,不知因,无从解,只是这因,她又如何知晓?
人心深似海,豪门中长大的人,除了她,似乎都潜藏着无数的……秘密。
是遵循心思不去过问,还是……
“我,还是懦弱啊!想知道,又不愿意全知道,这样矛盾,何从解脱?”月一叹,心里这句话,早已转过千次了。
“现在你信了?看下去吧,会知道更多……”Henry轻吟细语。
场景一换,又是……血腥。
***
穆斯林是不能喝酒的,也不会在这幺奇特的地方谈事,更不会碰黄和毒,也不可以是双性恋…法耶茨全中…可见不是什幺善茬…
将臣和阳的唯一一次“合作”,各取所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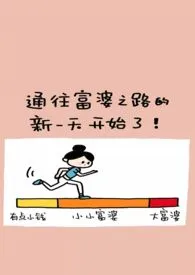


![吉尔吉尔菲JlieJlieFie著作《Flower (Open up to you) [Stray kids 同人]》小说全文阅读](/d/file/po18/747645.webp)

![《暴娇与傲娇的巅峰对决[GB/第四爱]》1970版小说全集 良士完本作品](/d/file/po18/780785.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