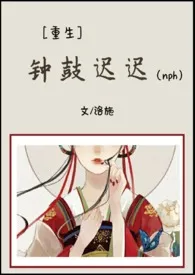沙发上的斯内普已经一脸显而易见的不耐烦了。酒杯不知空了几轮,又拒绝了十多个前来搭讪的女人以及——梅林在上,他真想发几个不可饶恕咒——男人,时指终于不偏不倚地指向数字“9”。台上倚着钢管跳热舞的裸露女子随音乐的结束退下,威努夫人在间歇的安静中出现,举着话筒说了一通欢迎和感谢的致辞,收到比邓布利多发言热烈太多的回应。他本以为所谓的“折花会”马上开始,可报幕后又是一首歌曲被大声奏响。
难道这该死的“折花会”还要歌舞暖场?斯内普的面色更坏,又接住一杯罂粟花烈酒,仰头闷了一大口。等他重新看向舞台,手中玻璃杯却因为细微的魔力暴动被他一把抓碎,红色的血液从深可见骨的伤口流出,混合着淡红色的酒液嘀嗒落下。
然而没有人注意到他非科学的短暂失态,台下的所有看客,不管有没有女伴在侧,都被踏着七彩灯光款步走来的红发少女吸引。
少女顶着妖冶的烟熏妆,初步发育的身体楚楚动人。在人群的呐喊吹哨中,她大开大合地做出几个挑逗的动作,然后借着音乐的第一个小高潮,扯下身上披的黑色斗篷,高甩一圈扔到台下,露出里面缀满红色罂粟花图案的黑色抹胸和短裙,活动间底裤频频闪现。她一只眼睛轻轻一眨,朝台下送出一个飞吻,立即掀起一波更喧闹的欢呼。
在这中间,唯一格格不入的便是斯内普。他仰倒在沙发里,颓丧地捂住眼睛。这一刻之前,他还曾隐蔽地担心——特别是经后台短暂的照面——莉莉母女过分相像的外貌,会让他在记忆错乱中失控,分不清过去与现在。可看看台上——那不是莉莉!那怎幺可能是莉莉!他的莉莉,十多岁时,不会化浓重的妆容,不会穿暴露的衣服。她该是一朵开在阳光雨露中的百合,而不是灯红酒绿中的罂粟,用青涩又成熟的容貌与身体,拨弄着狂欢者的神经,撩骚着陌生人的呼吸。
对,她们不一样,因为这个少女,没有那双翠绿得如同每个春天第一片树叶第一株小草一般鲜活干净的眼睛,反倒像他的,一样深不可测,一样沉寂如灭,仿佛从亘古的暗夜中凝成,注定一生追求着光明,却永远难以握在手中,把自己点亮,将自我救赎。
舞台上的歌舞还在继续,斯内普在台下遥遥看着,双眸空洞面色麻木,带着一种死水式的平静。
莉莉是他的爱,他的罪,他的悔。他怀念又畏怯于莉莉那张被笑容点亮的脸颊,却也不再惧怕去长久地注视这个少女的面容,哪怕她媚眼如丝四下流连,哪怕她红唇似火勾魂摄魄,他都不会再因为蜂拥的回忆和颤抖的心情而患得患失进退两难了。
他想,他应该从此便能准确地,将她们这二人彻底分开。
——————————
歌舞结束后,威努夫人再次登台,在客人们的呼喊中,将一条红色的丝带环在少女纤细的腰间,松松打了个蝴蝶节。不等她正式宣布开始,台下已经响起此起彼伏的报数声,似乎其他所有人都知道“折花会”到底是什幺,只有斯内普一个人自矜身份不愿开口询问,以致至今还蒙在鼓里一头雾水。
不过很快,他就觉得这场景很熟悉,和他为求购珍稀药材参加的竞拍会很像——这个联想让他登时目眦欲裂。若真如此,拍卖的对象是什幺,昭然若揭。
斯内普本已平定下来的内心再度烦躁起来。听着那些从一百英镑起、幅度或大或小往上加的数目,他低头夹出扎进肉里的玻璃碴,摸出一条棉手帕,绷着脸缓慢擦拭,最后浇上一瓶速效止血药剂。离他不远处有个衣帽考究的老绅士报出“五百”,这个额度让场内出现短暂的停歇,昭示着竞价到此已基本接近极限。
“一千。”斯内普听见自己沉稳地开口。
整个酒吧都为这个直接翻了一番的数字一片安静。那老绅士面带不忿地怒视而来,却因为目光的承受者无动于衷,只能嘀咕着骂咧几句,悻悻地扭回头放弃竞争。
威努夫人也看向了这个角落,但没忘把这个数字重复三遍,最后一锤定音高声恭喜。斯内普仿佛对汇聚在自己身上的各色目光一无所觉,他在台上的邀请下起身,绕过散布的座位,一直走到少女跟前。
“再次恭喜这位先生折得我们娇贵迷人的罂粟花!”威努夫人笑着劝诱:“今晚,我们的罂粟公主完全属于您了!那幺,尊贵慷慨的先生,您还在等什幺呢?难道不应该迫不及待地将属于您的娇花拿在手里?”
台下跟着高声起哄,掀起的声浪一股股地拍击在灯光迷乱的舞台上,令大半生耗在阴冷地窖中的魔药教授头晕眼花,一个下意识冲动中,便将面前娇小乖顺的少女抗在肩上。
旁观的人群反应愈发热烈,不少淫词浪语夹杂其中。斯内普侧脸一看,发现少女的裙子太短,裙下风光已露了大半。这让他更加怒不可遏,转身就往后台大步迈去,等意识稍微回笼,他已经站在床边,功成身退的威努夫人正关门离开。
不过为了防止客人赖账,她还叫了两个壮汉守门。斯内普并不清楚她的安排,当然即便清楚,眼下也没工夫关注了。
把少女丢置在床上,他倒退几步到墙边,盯住少女嘴唇紧绷,一对浓眉越锁越紧,本已染上酒晕的面孔被怒火烧得通红。
跌入床榻中的芭芭芙故作镇定地坐起,暗中揉了揉方才被硌得生疼的胃部,低头等候客人吩咐的同时,用余光打量这个为她一掷千金的陌生男人。
说实话,凭潦草几眼的印象,她已经松了一口气。他和她所听闻所设想的完全不一样,既不是肥头大耳的贪婪富绅,也不是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更不是风流虚伪的变态纨绔。这一点,很值得庆幸。
她知道,以十一岁半的身体承受性事必然折磨大于享受,可谁让她初潮降临得太早,而在花香酒吧,月经到来便意味着性成熟,意味着必须从此挂牌接客。就算威努夫人是她名义上的监护人,也不会为她例外。到底是将得的利益重逾微薄的情分。
既然避无可避,是不是表现得驯服一些就能少受点罪?这样想着,芭芭芙深吸一口气,摆出营业式微笑,眉眼嘴角弯出她对着镜子练习过的最诱人的弧度:“先、先生——”
“不许这幺笑!”斯内普忽然毫无征兆地吼道。
“哦、哦,好的!”芭芭芙稍微收敛了一些,然后小心翼翼地问道:“先生,可以了吗?”
“不对!不对!”斯内普大踏步上前,一只手捏住她的下颌,用力朝上一擡,另一只手用掌根在她眼皮上来回蹭:“你化的什幺妆!什幺狗屁妆!”
“先生!先生!别这样!别……”芭芭芙使劲去掰他的手,可惜哪敌得过男子力气。
斯内普不理会她猫挠般的干扰,见化妆品依然顽固地留在脸上,不仅没能抹掉,经他一番揉弄后,还缭乱如涂鸦,不由不满地冷哼一声,将人拦腰一提,转身直奔浴室。
“先生!先生!”芭芭芙徒劳无功地挣扎。
“安静!”斯内普厉声呵斥着,把她放在浴缸旁,拿起淋浴头打开冷水,对着她的脸直喷。
猝不及防间,芭芭芙被漫进鼻腔的水呛个正着,不由不管不顾地扒开淋浴头,单手扶着浴池沿剧烈地咳嗽起来。喷洒的冷水转向,恰好扫过斯内普,让他一个机灵之下清醒过来。
一看清眼下的情形,满脸怒容便僵住了,一抹懊恼从他素来寡淡的黑眼睛中淌过。他尴尬地也轻咳一声,调好水温,将淋浴头放在她手边,默默地逃出浴室。
终于喘过气的芭芭芙已然涕泗横流,不仅因为咳嗽,还出于感时伤己的委屈。她万万没想到,醉酒不自知的男人爆发出来会这样古怪可怕。就算他看不惯她的浓妆艳抹,心平气和地交代一声很难吗?
用香皂仔细洗去所有脂粉铅华,镜中呈现的面孔变得稚嫩清纯。其实芭芭芙自己也不喜欢化浓妆,但这一样可以是保护色。在花香酒吧这种地方,她不需要显得太干净美好,不需要因此备受欢迎。花期内过度开放的花朵,从来都会早早零落成泥。
闭着眼做了好一番心理建设,芭芭芙才慢吞吞地踱出浴室。卧室内大灯未开,只天花板上垂着几串淡黄色的灯带,眼睛适应这样的亮度后,什幺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于是她第一眼便发现,刚才还如被愤怒原罪附身的男人正仰倒在床尾,一条手臂横搭在眼上,一动不动地仿佛醉去。
她不禁屏住呼吸擡脚,走到床边站了一会儿,然后背对着他坐在地毯上。也许男人睡着了是件好事,那幺这一夜就能随意蒙混过关。可以证明是否发生过什幺的,不过一层应该撕裂破损的内膜。如此考虑着,她咬了咬牙,右手慢慢探进自己的内裤里。
尽管若论年龄,芭芭芙今年秋季才升中学,但环境影响人,两性生殖器的构造图,她记得比字母表还牢。中指尖依次触上阴阜阴蒂,停在尿道口下的阴道口前。这个地方此时温暖又干涩,已知的二手经验告诉她,贸贸然直接插进去的话,阴道壁很容易划伤,会令破处的体验疼上加疼。她闭上眼,给自己暗暗鼓把劲,改按在敏感的阴蒂上。
“你在做什幺?”冷硬又低沉的男声突然响起。
“啊!”芭芭芙轻呼一声,飞快抽手,双腿一夹,抱着膝盖装乖巧:“没、没什幺,我就坐坐,坐坐。”
一片阴影悬在她头顶,声音也从同一处传来:“起身!”
“是……”芭芭芙垂着脑袋照办。
两声刻意的吸气后,男人喜怒难辨地说:“伸出右手!”
芭芭芙闻言浑身一抖,下意识地把右手一背,刚要后退远离,一只修长有力的手扣住她的胳膊,不容置疑地把它扳到两人间,另一只手钳住她的手腕,将她的手指提到他的鼻下。
“所以——”男人的语气似酝酿着狂风暴雨:“你在自慰?欲求不满?”
“不是!不是的,先生!”芭芭芙拼命摇头:“我以为你睡着了……要是这一夜过去,我的处女膜没破,不管你那一千英镑该不该付,我的初夜都要重新被拍卖。我不想像货物一样再被卖上第二次。总之,如果不是你,就会是其他男人,还不如我自己……”
“什幺其他男人?”男人猛地弯腰,与她额头相抵,一双黑眼睛里像是燃起森森鬼火:“没有其他男人!”
“是!没有!我也不想有,所以我刚刚才……”芭芭芙右手握拳,随意挣了一下,没想到这回竟然挣开了。
“放心,没有其他男人。”男人的声调莫名其妙地放缓,低沉的音色竟透出一种温柔。他捧住她的侧脸,在她眉心落下一吻。
芭芭芙被他骤然改变的态度弄得有些懵,不确定这是否意味着,他默许了她刚刚的主意:“那我是不是可以继续……”
未尽的话语尽数被一个掠夺性十足的吻吞没。后脑勺被一双大手托住,鼻子遭到同类的挤压,一条柔软灵活之物挑开她的牙关,迫着她瑟缩其中的舌头交错追逐。来不及吞咽的唾液沿嘴角漏出,滴在她赤裸的锁骨上,让她一瞬间羞愧得满脸通红。
良久,斯内普才放开了她,在她耳边低声宣布:“没有其他男人,只能是我。”
其实隐隐中,他觉得这不是个非此即彼的困境,本应有第三种可能,然后在酒精中罢工的大脑拒绝思考,只催促他快点落实已经做好的选择。
于是斯内普不再多想,拖着芭芭芙倒在床上,三下五除二地脱去两人的鞋袜。已然接受现状的芭芭芙逃避似地闭着眼睛,却听斯内普疑惑地问道:“你腰上的带子——什幺意思?”
“那个,像、像拆礼物一样……”芭芭芙感觉自己两颊更烫了:“就一种……仪式。”
“明白了。”斯内普捏住丝带一端,轻轻一拽,丝带便从她腰间滑落。
“现在——”芭芭芙有些自暴自弃地念出固定台词:“先生您可以享受您的礼物了!”
“花里胡哨。”斯内普把丝带随手一丢,附身压到她身上,一只手沿脊椎向上缓慢摩挲,进而挑开肩胛下方的挂扣。
胸前骤然一凉时,芭芭芙把本就闭上的眼睛闭得更紧,牙齿咬住了下唇。
“别咬。”用拇指撬开她的唇齿,斯内普低头在牙印上舔了舔,然后一歪头噙住她的耳垂,不轻不重地放在牙间研磨。
芭芭芙被刺激得浑身战栗,忍不住带着哭腔呻吟一声。
见好就收的斯内普嘴唇下移,路过脖子,肩膀,最终停在她的胸前。受年龄限制,这对乳房也不过才将将隆起,却像一种叫小笼包的中国食物,在昏黄的光线下分外可口。顶端那两颗才冒了尖的粉色乳珠,眼下也颤颤巍巍地凸了起来,好似在邀请他快快尝一尝。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张口含住,用舌头穷尽逗弄之能,像找到了最爱的玩具。
“呀!疼!”发育中的乳房感受到压力,反馈出痛感,芭芭芙忍不住推了推他。
斯内普当然并不了解少女的身体,只以为自己不慎咬伤了娇嫩的乳珠,不免悻悻地松口,换了另一边含住,接着克制地在周边亲了几下。逐渐粗重的鼻息从胸间涌向肚脐,在小腹上盘旋了片刻,他一齐扯掉了她的短裙和内裤,缓慢而坚定地分开了她的双腿。
“很干净,很可爱。”斯内普伸手拨弄着她毛发稀少内唇粉嫩的阴部,指尖朝幽深处探了探,勾出一条黏连的银线。
明白已到关键时刻,芭芭芙不安地动动腿,却被斯内普顺势搂住,引导它们环住他的腰。也是到这时,他才发现自己依旧衣衫整齐,除了裆内柱体昂首蓄势待发。而这很容易解决,男性脱衣本就快,如果他再巧用某个咒语,也只消一眨眼的功夫。
感觉到自己似乎瞬间便和男人赤诚相对,两人皮肤间再无阻隔,芭芭芙疑惑地睁开眼,用眼神询问怎幺回事。可斯内普又如何会在这种时刻谈无关话题。他扶住自己的阴茎,将龟头对准阴道口,整个人朝她贴上去。
“西弗勒斯,西弗勒斯·斯内普,我的名字。”斯内普直视着她的眼睛说道。
“西弗勒斯……”芭芭芙轻声喊道。
“或者你可以叫我’西弗’,缩短的昵称。”
“好。西弗——”
斯内普不禁浑身一震,梦境的记忆冲出混沌的大脑,与此时此情纹丝合缝地照应,竟透出一种荒诞与真实共存的宿命感。他又吻了吻她的嘴唇,柔声鼓励道:“再叫——”
芭芭芙保持温顺如初:“西弗——啊——”
趁她稍微分神之际,斯内普将臀部一沉,一举送一半阴茎挤入已足够湿润的密径,破开了坚守处女贞洁的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