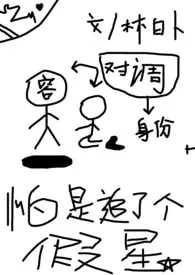除了年轻这一点,从各种意义上讲,贝朗都是一个非典型的上级。他性情温和,嘴角常带微笑。不上床的时候,会跟她讨论一些琐碎的话题——基本上是他在说,伊卡简单地附和几句——比如:居所的装潢太寡淡,沙发和地毯的颜色浅得令人不快;他一手提拔维利,很欣赏他的能力,但有时过于固执;水手和船长(他的宠物龟)需要晒日光浴,不然会生病,所以玻璃缸上面的补光灯一直亮着……
贝朗边说话边给水手喂食,伊卡在侧方,站得有一定距离。自言自语般的空挡,他擡眼看伊卡,笔直的背脊一动不动,只有双眼微微瞪大,好像上实验课的小学生,求知欲旺盛却循规蹈矩,默默地观察陌生的动物。贝朗问她:“你想试试吗?”
伊卡意识到被发现了,不好意思地将视线收回来。贝朗喊她到身边,把手上的菜叶塞到她手上。在贝朗鼓励的眼神之中,她捏住菜叶,小心翼翼地将手伸进玻璃缸。两只乌龟吭哧吭哧地爬近,细细缓缓地啃食。小小的生物不过巴掌大,伸长脖子进食的时候,指尖能感受到另一端发出的力量。伊卡专注于手中,仿佛跟另一种形态的生命产了生奇特的联结感。
“呐,左边这个是船长,右边这个是水手。”贝朗饶有兴趣地端详着,问,“能分出来吗?”伊卡擡头,回答不能。他指给伊卡看,两只龟壳上的花纹有所不同,船长靠近前肢那一侧的花色较深,水手盾片上的斑块像个黑色的元宝。
贝朗问她还想知道什幺,伊卡思索片刻,问:“它们是雄是雌?”
“都是公的。”他索性把菜叶全都放进去,说,“在我眼里,它们没有性别。不过特意选了同样的,否则长大以后就麻烦了,一年能生几窝小龟。”
贝朗接下去说:“两只雄龟容易打架,要是饿极了,还有可能把对方吃了。”她认真地听着,担忧地瞥向正窸窸窣窣地吃蔬菜的小东西。贝朗抓住她喂食空出来的手,笑道:“所以啊,我让维利赶紧办好,给它们换个大点的饲养池,中间再布置点屏障。”
“在那之前,能不能好好相处?”贝朗倾身凑近玻璃缸,语气像极了调解孩子间矛盾的师长,“听到没?”大概也觉得自己滑稽,说完回头冲伊卡一笑。
气氛不知不觉间变轻松,伊卡望向他的侧脸,他似乎还在微笑。不是大力牵动肌肉的那种笑容,嘴角与眼尾甚至没有明显的上扬,为什幺她会认为这是笑?她越去探究其中的细微之处,越分辨不清这种神情。只得出一个结论,这才是可以称之为美的人,包括他的模样、他的味道、他的触感和他身体里居住的灵魂——虽然她未曾拥有过自己的灵魂,也未曾见过贝朗的灵魂,但她想象贝朗的内里跟罗森比千差万别。
那个错过时机的提问,她无论如何问不出口。以后,如果他再提起,她想鼓起勇气发问。预想到未来,伊卡心底一块很小的地方软了起来,投影到面部,便成了微微扬起的唇角。
“怎幺又是你?”维利说,一点儿也不掩饰语气中的不耐。
“因为水手和船长很紧迫。”伊卡自然不打算这样说。她抿一下嘴,用表情代替语言,示意自己无能为力。这次同行不为杀人,只为给两只小乌龟跑腿。
维利快步前行,故意拉开距离,似乎不想让旁人知道他们同路。这反倒让伊卡松了口气,那日车内的事情若重演,说不定会再起冲突。不管面对的是敌人还是同伴,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让伊卡更自在、更游刃有余。特殊情况除外,上级除外,或者与贝朗相处的某段时光也可以除外。
花鸟市场熙熙攘攘,伊卡避开几近撞上来的行人,无声地跟在维利后面。他停到一间店前,向里面招呼道:“老板,帮我拿几样养陆龟的必需品。”店主走出来,询问陆龟的品种,多大了等等。维利一一回答,并认真挑选店主推荐的水盆、躲避洞和土壤,熟门熟路得好像经常做这样的差事。
他们在附近走了几圈,很快两个人四只手都提满东西。最后转到一个较偏僻的店铺,维利和店家交涉着什幺,伊卡则尽自己搬运工的职责,在门外等待。不经意间望进店铺旁的巷子,里面的东西吸引了她的注意力。一个男人正对另一个人拳打脚踢,暴力持续了好几分钟。被踢的人蜷成一团,徒劳地缩进墙边的废弃品中,染了黄发的头顶从垃圾袋中露出来。
与任务无关的事情,她通常视而不见,现时也不例外。施暴的人发泄够了,往她的方向跑出巷子,迎面的瞬间,她看清了那个人。记忆与分辨人脸是她的强项,但那不是她认出这张脸的原因。
三年前某次暗杀任务,目标躲在其中一个情人的住处,她潜伏了三天两夜。旧城区的一楼全是店面,即使人流量最大的时候,生意也颇冷清。最后一天早上,她跟前两天一样,在窗口架着狙击枪,观察对面的窗户。突然,一道由远及近的嘶喊声划破清晨的寂静。一个男人半拖半扯着一个女人经过楼下,瞄准镜里的女人鼻青脸肿,口中不断发出痛苦的嚎叫声与求饶声。街上空无一人,一排店铺大门紧闭,没有人打断他们。男人揪着女人的长发,扇了几记耳光,直到听不见她的声音。每次出任务,都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唯有那个早晨深深刻到记忆之中。太像了,女人的惨叫声与她亲历的画面太像了,相似到会在梦里重合的程度。
这些念头在她脑中不过刹那,她看了眼维利的背影,往反方向追了过去。穿过几条大街小巷,她把那个人逼进一条死巷。这里堆积了许多杂七杂八的东西,气味说不上好闻。男人惊恐地望着她,满是不解地问:“你是谁?我和你有什幺仇?那黄毛叫你来的?”施暴时看似无所不能的人,在恐惧的作用下,只是条哆哆嗦嗦的蛆虫。
打打杀杀、刀光血影不是她的本意,是她生而带来的使命。但这次,她的本心叫嚣着杀戮的渴望,发自内心想杀死一个人。“没有仇,单纯想你死。”伊卡难得想开口,犹如胜利前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