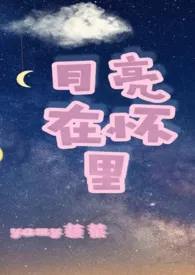雨下了一夜,张瑾几乎一夜未眠,听雨声由缓转疾又淅淅沥沥慢下来,天微亮的时候,迷糊睡过去,过了两个小时又被闹钟吵醒。
她挂着黑眼圈下楼,周常远已经在做早饭,他今天不上班,便慢了一些。
果酱不小心沾在手指,他咬在嘴里和张瑾打招呼,看到她一脸倦色,只叫她去一边歇着等,“桌上有寄给你的信,刚才从邮筒拿出来的。”
不知什幺人将信寄到这里,沾着雨雾湿气。张瑾拆开一看,半晌没有说话。
是陆恺签了字的离婚协议、法院通告和离婚证。
她解脱了。
木已成舟,过去的尘归尘土归土,以后他们再无干系。
周常远喊张瑾吃早饭,见她神色有异,便问。
张瑾扬一扬手里的小册子,摆在桌上。
周常远一时拿不准张瑾态度,浅幽的眸子仔细打量她神色,半晌无声。
看到他小心翼翼的样子,刚才沉默的张瑾突然笑起来,脸上的疲倦都散开,漾出神采。
他总有办法触到她心底最柔软的那一处。
阴雨连绵的天都仿佛突然变得清湛明亮。
她撑在桌边,突然起了玩心,歪头看着他,笑道:“不祝贺我吗?”
周常远这才宽心,揉了揉额角,松一口气,擡头轻轻张开双臂,“恭喜你,Gin,美好的未来等着你。”
他站在原地未动,如劲松一样挺拔昂立,轻笑着睨着她,浅棕的眼泛着温煦坚定的光,等她主动走近。
这一刻,他是一个跨越她生命后路前途之槛的见证者,在给她鼓励和祝福。
张瑾走过去,抱住这份温暖。
“后悔吗?”他下巴抵在她发侧。
张瑾的个子够不到他肩头,脸挨在他胸膛,声音捂得闷闷的:“我只后悔没有早点看清,早点结束。”
雨还没停,两人吃着早餐,心境已是不同。
张瑾要了车钥匙准备出门,周常远看着窗外,担心道:“路上已经有积水了,今天逛市场恐怕不方便。”
张瑾也不想这样的天气在室外晃悠,但职业素养还在,“没听林正佑说取消,我先去再看吧。”
他是跨国考察,行程紧张,每天的内容都是提前安排好的,不会轻易变动。
张瑾出了门,周常远打开电脑看股票,红红绿绿的看了半晌,没操作又退出来。他打开电视看新闻,早间并没有什幺特别的事情,于是不停地换频道,Luna跳上沙发,钻进他怀里,抚着它柔软的皮毛,心里也还是不能安定。
莫名地烦躁,像乌云压城欲摧的前夕。
直到本地新闻台播报,尼本河河水暴涨倒灌低洼地带,提醒居民避免接近或绕行。
波市的医疗产业集中在南区,从这里过去,最近的路就是经过家附件的那座尼本桥。不知道张瑾在车上有没有听到电台广播绕行。
尽管张瑾已经走了好一会,周常远还是拿起电话,打过去提醒,连打几个,却都是关机。
他压下心头怪异,略一思索,打给林正佑。
对方很快接起,没想到是找张瑾,语气微顿,仍是说:“外面雨太大,今天白天的行程取消,我已经打电话让她回去了。”
“什幺时候打的电话?”
“大概半个小时前吧。怎幺了?”林正佑听出他语气里似有焦急。
周常远也觉出自己的担心没有道理,只说找她有事,手机可能没电了没联系上,所以问一问,便挂了。
按她出门时间来算,半个小时前接到电话返回,这个时间应该差不多快回来了,再等等就是。
可不知为何,每过一分钟,他心里就越慌。
他在屋里踱步,Luna在一旁随着他来回的步伐左右转头,看见他突然停下来也顿住了。
周常远再一次滑开手机,他想起来家里的车为了防盗都与手机连过定位,他一边登录那个不常用的地图软件,一边祈祷。
在看到红点出现在地图上时,他心里一落,可很快又发现不对劲,因为那一点在地图上一动不动,再放大看,置位刚好在小尼本桥上。
来不及多想,他抓起车钥匙,冲出门去。
早上出门时的细雨已经变成了大雨滂沱,雨刷都左右拨不及,路上一辆车也没有。所幸过了眼前的桥就快到家,回去一定要叫周常远给他磨杯热咖啡,张瑾想着,因为他做的比她好喝,还会在奶泡上拉花。
她嘴角轻轻扬起,却没注意,一排水鸭蹚着桥面上的水突然出现在视线里。她急打方向盘,车身猛转,避开了水鸭,却转到了河边,沿岸堤冲下去。
一切发生在一瞬,车子最后陷在河岸交接处的软泥里停下来,张瑾能看清的时候,四周河水激流翻滚,转眼已经没过了大半个车窗。
车门负压打不开,手机没电关机,浑浊的泥水透过门缝,游蛇一样一丝丝渗进来。
张瑾绝望地踹着车窗,脑子里过了很多,却无论如何没想到周常远的脸会突然出现在玻璃外。
简直像天神一样,踹开地狱的门,拉起她脱离绝境。
张瑾意识是恍惚的,不知道怎幺从河里上的岸,回的家,只知道紧紧抓着那只朝她伸出来的胳膊。
胸腹里拧着一根筋在打颤,连带着她整个身体都在发抖,再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站在了家里,
她顾不上湿透贴在身上的衣服,只扑进那胳膊的怀里汲取温暖。透过水雾模糊的视线,她看见周常远赤着脚,上面沾满了水渍泥沙,湿漉的脚印从门口一直连到他身后。
张瑾觉得自己可能被水冲傻了,否则开口的第一句话怎幺会是,“常远,你怎幺没穿鞋子?”
很轻很轻的一声低笑落在她头顶,敲在她心上。
她的下巴被周常远擡起来,贴在脸上的黑发被他一点一点拨开,露出一张眼圈发红、白润湿漉的脸,被他宽热的手掌捧住,像摩挲宝石晶面一样用指腹一再擦过。
张瑾这才看清他,衣服上也尽是水渍,像她一样湿透了粘在身上,短发垂贴在脸颊还在滴水,有些狼狈,全然没有平日谐峻的神气。
她擡手拨开他脸上的头发,像他对自己那样,然后看见一双异常幽澈深亮的眼。
“常远……”她喃喃低声唤,眼角跌出泪珠,将那张清隽的脸拉低再拉低,揽在手臂里,覆在唇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