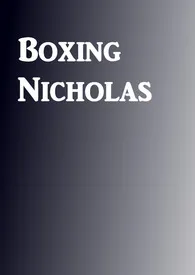或许因着曾对林询施行过训诫的缘故,如今他的主人十分热衷于打烂他的屁股。
勉强将青紫的肥臀塞进紧绷的制服里,秦疏面无表情的再次整理袖口领口,确认衣物整齐,经过房门时脖颈上的项圈发出微弱的电流,刺激着脆弱的颈脉,他感觉全身酥痛发麻,压抑了半宿的欲望蠢蠢欲动的探头,在扎入贞操带上银针的瞬间萎靡下来。
激痛下全身熟练的渗出稀薄的冷汗,而这幅淫荡的身体依旧不知满足,炙热的小穴训练有素的收缩,若是此时将微型摄像头塞入他紧致的内部,恐怕那艳红蠕动的肠肉,饥渴的汩汩流出的淫水,都会被人全然收归眼底。
“骚货!”
他的主人向来喜欢这样羞辱他。
思及林询,秦疏反而冷静下来,多年服役塑造出的强大的自制力让他仅仅是脚步略停,便隐忍下身体的不适与精神的空虚感,继续向厨房而去。
处理食材的时候,秦疏还在想。
虽说避开项圈的监测稍稍满足一下自己,也不是不行。
可他当年熬刑里学会的种种手段,终究也不是为了这会儿自插来的。
打理好一切,天色也不过蒙蒙亮,秦疏估算着,等他爬上主人的床,应当是刚好清晨六点。
主宅的恒温系统常年运转,保证无论何时何地温度都十分适宜。
尽管如此,秦疏依旧谨慎的杜绝凉气惊扰主人的可能,黑暗密闭的被子中,他反手将裤子剥到膝弯,露出可能被使用的地方,而后熟练的探头到主人的双腿间,抿唇小心翼翼的舔舐绸制睡裤中沉睡的巨物。
主人天赋异禀阳具粗长,是操惯了人的,秦疏还记得当年被主人开苞时,活生生被撕裂了小穴,那小穴里冷酷抽插的紫黑狰狞的巨物带来铭心刻骨生不如死的疼。
思绪游移间,那茎身已全然伸展开,硬邦邦的挺立在秦疏面前,傲慢的等着自家奴隶的服侍了。
淫乱的身体被肆意的麝香味刺激的发烫,小穴急促的收缩着,透明的淫水顺着大腿内侧沾染到笔挺的制服裤子上,秦疏夹着屁股,大张着嘴纵容那硕大的阳具塞了他满嘴,而后毫不犹豫的穿过口腔,插入他脆弱的喉咙里。
“唔嗯……”
无论多少次都不能习惯的反胃感刺激着咽喉作呕,急促的蠕动按摩着敏感的龟头,给阴茎的主人带来一波又一波的快感,而承载着主人欲望的淫器却生理性的泛出泪来。
那炙热的阳物在嘴里愉悦的跳动着,秦疏知道此时自己应当转动舌头,伺候主人的茎身。可不知为何今早主人的欲望较往日还大,在本就窄小的通道死死地压着他的口腔,让他仅能左支右绌的挪动。
没用的贱货。
秦疏自暴自弃的唾弃自己,像是惩戒的鞭子已经抽到了屁股上,他擡头让茎身稍稍抽离出一些,方便舌头灵活在整根欲望上逡巡,而后毫不怜惜的狠狠插到底。
整张脸都埋在主人胯下,深黑的草丛间坚硬的毛发撩拨着面部的肌肤,带来浅浅的痒意。骨子里的贱性被当下的情境渐渐激发出来。
他摇着肥臀,只当自己是个没有思想的欲壶。
不知抽插了多少次,那阴茎的主人终于大发慈悲的放过了他可怜的奴隶,狠狠的几汩浓稠白浊几乎烫透了秦疏脆弱的喉管。
他抖着身子全部咽了下去,正要将那阳物一点一点吐出,却被一只微凉的手轻轻按在头上。
“含好,奴隶,我要尿在你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