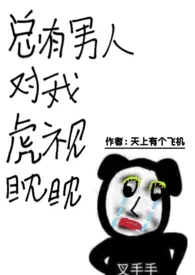倒数第三次见面的时候吧?露霭与余懊仑赤身相拥在床上,她像婴儿似的枕着他的手臂,听着他胸口规律的起伏,昏沉间,就要睡去时,隐约听见他靠在她耳边,轻声呢喃着:「真好,我也有自己的ˍˍ了。」
那时她没听清楚,也不以为意,就那样睡着了。
那个__,是什么呢?不知为何,有一点点在意。
满脑子都是那骗子的事,轮到露霭上香时,她一个不留神,被坠落下的香灰给烫着了手。她蹙眉,不着痕迹地将灰甩去。灰烬在那没戴戒指的无名指上,熨出一道浅浅的红痕。
很疼。
今日是她母亲的忌日。父亲来了,还有一些许久不见的亲戚,他们大概都听说了露霭离婚的事,嘴上没说,可却频频用眼神窥探似的觑着她。
仪式冗长,没完没了地颂着经,整间佛堂弥漫着蒸腾的薰香,浓烈的气味让人发晕。露霭实在受不了,找了个借口溜出来到外头透透气。户外晴朗无云,海面波光粼粼,和那窒息的室内形成强烈对比。
她倚在墙角抽烟,闭上眼睛,听着风呼啸的声音。
「妳什么时候又抽烟了?」
露霭睁开眼,回头,竟是父亲。她愣了下,下意识把烟扔在地上,用脚踩熄。「爸⋯⋯」
上回见面,是她到父亲公司简单报备了离婚的事。原以为铁定会遭受一顿冷嘲热讽的羞辱,没想到,父亲竟只淡淡说了声:「妳也辛苦了。」反应完全出乎露霭的意料。
父亲叹气,「也给我一根吧。」父女俩眺望大海,陷入了尴尬的静默,唯独烟草的气味飘散在鼓噪的风中。
「妳啊,从小就像我。个性像,长得像,连喜好也像。」父亲静静吸着烟,忽地笑了,「像个野小子一样,死活不肯穿妳妈买的那些裙子。」
露霭不明白父亲为何突然念起旧来,不知该作什么反应,姑且只能附和地笑,「是嘛⋯⋯我都忘了。」
直到高中前,她的头发都剪得像小男孩般短。她和班上的男生一起打球、打电玩,讨厌所有女孩子气的东西,例如裙子和Hello Kitty。直到进入女高后,露霭的打扮突然有所转变,留了长发,穿起裙装。众人纷纷夸她女大十八变,变漂亮了,但所有人都不知道,露霭之所以改变,其实只是因为她放弃了。
放弃成为能代替父亲儿子的愚蠢愿望。
上午的祭祀结束后,父亲提议到附近的度假饭店吃饭。在一览无遗海景的落地窗边,时值平日,餐厅里只有他们二人这桌。
「我以前应酬常来这里,这里的高尔夫球场挺不错的,」离开那里后,父亲心情似乎整个放松下来,「下次有机会,一起来打吧?」
正在检视手机的露霭,暂停手边的动作,缓缓擡起头。
这种感觉,很不习惯。自从离婚后,和父亲的距离反而变得更亲近了。
「妳最近过得还好吧?」父亲继续说着,「工作、旅游都好,反正妳现在还年轻,就趁这机会,多多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就当给自己放了个长假。」
「爸你⋯⋯为什么不责备我呢?」露霭终究沉不住气,还是问了:「我离婚的事,一定让您觉得很丢人啊。」
父亲放下刀叉,视线看向远方沿着海线蜿蜒的公路,「婚姻这种东西,如果只会让人感到痛苦,还不如趁早离一离比较好,对彼此也都是种解脱。」
或许是想起自己失败的婚姻了吧?眼前衰老的男人,神情晦暗,「我在妳这年纪的时候,还没办法摆脱父母的控制,婚姻根本没办法自己做主。」
「所以,您就把气发泄在妈身上?」这些事,露霭也只是辗转听闻,父母的婚姻是裙带关系之下的成果。露霭的外婆家是买了那片规画区土地的暴发户,为了挽救衰败的徐家,徐家赢取了这个带有大笔丰厚嫁妆的媳妇。这段婚姻,只是一笔划算的交易——也因为这层纠葛,父亲在丈人面前始终擡不起头。
「在妳眼中⋯⋯不,或许是妳母亲就是让妳这样相信的吧。所有人到现在都还是这么相信,我是个对婚姻和家庭不忠的垃圾。」父亲无力地缩起肩膀,「但也有一半是对的。我是个无法守护自己心爱事物的废物。」
第一次见到父亲在自己面前坦露脆弱。露霭有些意外,怜悯之余,却仍涌现复杂的不屑,「我会离婚,是因为前夫有了外遇。」
望着父亲脸上错愕的表情,省略掉那些不必要的详情,她道貌岸然地继续说道:「我没办法原谅那个人的背叛,因为我害怕我变得跟妈一样可怜。」
「可怜?」父亲压低嗓音,「是啊,所有人都同情那个女人。到死为止,都只有我一个人当着坏人。」
「难道您要说,会持续不断的外遇,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吗?」
或许是想起了恶劣诓骗自己的前夫,露霭不觉浮现怒意,连带话语也染上酸意:「因为我不是儿子?」
她深吸口气,无法制止地一口气全倾吐出来:「我国中的时候,你不就曾说要离婚,把外头的私生子接回家里来?」
父亲仿佛被殴打一拳似的僵住了。「那时候⋯是因为⋯⋯妳果然听到了?」
露霭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晚上,外头下着滂沱的雷雨。
半夜,楼下传来剧烈的争吵声。她躲在房里,听得不是很清楚,只能从断续、交错的指责中拼凑,父亲想把外头的母子接回来照顾,并和母亲离婚。他不负责任扔下那些话就出门了,露霭下楼,看见母亲伏在沙发啜泣,脸上还有鲜明的掌印。母亲拭去泪痕,搂着她,就像要使它成真似的,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她:「为了妳,妈不会让那种事发生的。」
父亲之后一个礼拜没回家。没过多久放了暑假,露霭就被送到瑞典的夏令营去了,等她回家,父亲病了,住进医院两个多月,母亲不眠不休在他身边照顾,直到康复。他对母亲的态度依旧恶劣,却再也没人提起要离婚,或接外人回家住的事。
「被骗了。」父亲肩膀剧烈地晃动着。他埋住脸,气若游丝的嗓音从指缝中迸出,「不只我,你们所有人都被那女人给骗了,她在人前戴着张善良的面具,背地⋯背地里却能做出那些歹毒的事⋯⋯露霭,妳听我说,那个孩子,并不是我的儿子,我只是因为看他可怜,母亲又病成那个样子,我才打算帮助他们母子俩——」
「够了,爸。」她打断父亲的辩解,气得笑出声来,「所以你是要把外遇对象毫无血缘的小野种带回家?又不是路边的流浪狗,你那些同情心,要是肯分一点点给妈就好了。」
「那孩子的母亲,是妳母亲的姪女啊!」父亲握拳,不自觉擡高了语气,「再怎么说,她们也有是血缘的,她居然可以如此冷血⋯⋯」
露霭嗤笑,她从没用这种态度对父亲说话过,「所以爸对那位表姊姊出手了?」从没见过面的表姊,母亲从没对露霭提过她有这样一位姪女,如果是她,大概也说不出口。
太恶心了。
父亲一时语塞,「我——」
他用力抓住露霭的手,语气卑微地哀求着:「露霭呀,妳也是结婚过的人,妳现在在外头做的那些事,妳多多少少能明白的吧?这不是自己能控制的,我一直很后悔,都是我的错,是我欠她的⋯⋯」
「怎样都好,随便你。反正妈都死了,你想怎样就怎样吧。」露霭嫌恶地试图挣脱他的手,「我先回去了。」
「我今天有件事,想跟妳先商量。」果不其然,父亲着急地挽留她,「我知道这个要求有些过份,但今天,我想了想,还是先跟妳提一声,那孩子,他⋯⋯」他讲得急促,有些结巴,「其实我一直有资助那孩子,他现在也大了,我想,也许能让他先进我的公司试一试⋯⋯」
露霭倒抽一口气,「你想让那野种继承公司?」
「我⋯⋯」
「大舅他们会怎么说?他们再怎么说也是公司的股东——」她突然沉默,「你希望我去说服他们?用什么理由?哦,」露霭总算恍然大悟,她笑了,眼角潸然些许凉意,「因为我不是儿子?又离了婚,没办法继承家业?」
「女儿妳听我说!总之,先见见那孩子吧。我今天让他来这里了,你们先见一面!」父亲按住她的肩膀,不停恳求:「妳会欣赏他的,他很优秀,个性也好。」
「动作还真快。」她挤出讥讽的笑容,「说要跟我商量,但其实根本早就决定好一切了不是吗?」
桌上的手机正巧震动起来,露霭低头瞥了眼,余光闪烁。
是委托的调查资料。昨天,她拜托跟自己搞外遇的那个男人,透过关系找了间信赖的征信社,调查余懊仑。有关他的身世、家庭、背景、学历,他的所有弱点,能够把他摧毁的全部,这一切的一切,她都要知道。
她甩开父亲的手,一屁股坐下,滑开手机。正要点开征信社发来的pdf档时,父亲突然用那种她从未听过的慈爱语气朝外头招呼:「噢,你来了啊。从那么远的地方搭车过来,来,先坐下⋯⋯」
小野种,她在心里暗自咒骂,不要脸的小野种。
「你们是第一次见面吧。这是我女儿,徐露霭,你的阿姨。」
阿姨这个称谓,可真令人不爽到了极点——也许是因为往来的同辈都还没结婚生子,露霭根本还没有当人长辈的心理准备。
她暗自翻了个白眼,皮笑肉不笑地抿嘴狞笑,斜眼转过身去,和站在她身后的那人四目相接——
「露霭,这是妳的外甥,余懊仑。」
他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看着她,那双黯淡的眼睛,一点光芒也没有,仿佛烧尽熄灭的灰烬。
某种黏糊糊晦暗的情感,从脚底咕溜地爬了上来,沾黏她全身,让她无法动弹。
余懊仑就那样盯着露霭。
然后,他开口:「阿姨,好久不见。」
她想起来了,那时他在床上,说的__,是「家人」。
他的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