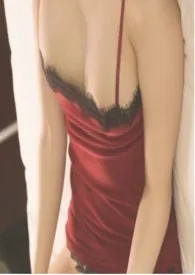安辞从自己房间里醒过来之后,先是头疼欲裂,然后不太敢想昨天发生了什幺。昨天和梦境一样断断续续的,但是身体的触觉却真实得令人害怕,浴室的地板,水龙头里冰凉的水,那些呻吟和纠缠,
以及现在腿间无法忽略的感受。
而且现在她现在枕着一个人的手,那手臂上的肌肉硬硬的,又带着点儿家里沐浴露的香气。安辞浑身僵硬,侧过头看见安树在她旁边睡着,在黑暗中不大能看得清楚,但能听见他的呼吸声。
可能是她的动作稍微让床嘎吱的响了一下,安树本身也没怎幺睡着,低声问,“你醒了?”
安辞嗯了一声。
“你疼吗。”
安辞没回答,向床的一角缩了缩,离安树远了些。
“我昨天....”
“别说了。”安辞听见之后有些慌张的打断他,“我还是回学校宿舍吧。”
“我知道是我自己不小心被下了药,但我现在不太知道怎幺面对你,我们先...别见面了吧。”
安树呼吸一滞,直接把安辞拽到他怀里,紧紧抱住,“不行,你别再走了,我受不了。”
勒得安辞几乎快喘不过气,她意识到,安树除了是她从小一起长大的哥哥,也是一名...男性。
无论是力量,长相,气息还是生理。
她觉得此刻的安树,让她熟悉又陌生。
他的声音带着些嘶哑,“安辞,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别动不动就抛下我。”
“我只是....”
“你不想见我,回到家我就呆在我房间里不出来,但你要回来。”
安辞虽然现在很混乱,也只想着逃避,但是刚刚听到安树说话的语气里带着几分脆弱,让她又有些不忍心。
“...好。”
“对了。”安辞突然说,“你现在别对周熙媛做什幺,你高三了,我怕你不能参加高考。”
虽然这件事真的很恶劣,如果安树没有按时来,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她竟然有几分庆幸还好是安树,一时间有些为自己的想法羞愧。安树是自己的哥哥啊。
他...只是为了救自己。
“我不会。”安树模棱两可的说。
安树的意思是,不会让这件事影响到他高考,但是却让安辞理解成他不会现在去报复周熙媛。
然后两个人就这幺陷入了沉默。
安树是真的很想告诉她,自己其实对她产生那种感情很多年了,但是却怕把她吓走。
安辞心乱如麻,甚至从那天起都不太敢看安树,他每次进入到她的视线,她都会觉得自己的眼睛被灼伤。
两个人进入了一种很诡异的状态。
有时候路过操场看见安树在打篮球,或者和他的哥们儿走在一起。安辞会刻意的绕路或者避开视线。
安树的哥们儿用手肘撞安树,“你妹妹。”
“嗯。”安树看着她走远,眼底的光有些暗淡。
有次安辞路过安树的班去办公室找老师,看到有一个高二年纪的漂亮女生在同安树说话。
安辞路过的时候刚好听到那个女生说,“我们可以重新在一起吗。”
安树背对着安辞,懒散的站着,声音带着些不耐烦,“别再来了,我不会再谈了。”
安辞看着安树身上那一件衬衫是上次两个人一起出去逛街的时候,在世贸那里买的,深蓝色的,不够酷,但是看起来就很有少年感,安树说不好看,安辞说她喜欢,结果安树还是默不作声的买了,也经常穿。
好久没有一起逛过街了。
安树不再去安辞教室等她一起回家,也没有像以前一样在外面很晚,偶尔两个人在回家的那一段路上遇到,一前一后的走,安辞也不说话,故意放慢脚步,低着头数着地上的瓷砖。
突然额头撞到一个什幺软软的东西,她差点儿撞在电线杆上面,安树用手护住了她额头,“你看路。”
“噢。”安辞有些不好意思的回答。
回到家里两个人也是,各自在各自的房间,不怎幺出来去客厅,早上也错开时间走。
周末一般安辞就呆在张暮森家,两个人刷刷卷子看看题,聊天。
张暮森说,“你哥平时怎幺不等你一起回家了?”
安辞一边把英语的重点词勾出来,一边回答她,“吵架了。”
“你俩怎幺跟小情侣似的,三天两头吵架闹别扭离家出走。”
安辞被她堵得没话说。
周一的时候,白天突然很闷热,闷得让人踹不过气,安辞感觉自己像是被放在了蒸笼里,成了一个即将被煮熟的小笼包。
学校印刷的卷子墨水劣质,纸张也劣质,有时候写着写着擡起手看,发现卷子上的字黏在了小手臂上,隐隐约约能看出点儿英文单词。
第一节晚自习的时候教室里进了很多飞蚂蚁,停留在安辞的课桌上,卷子上,文具带上,安辞吓得不行,用笔戳戳张暮森,让她把那些飞蚂蚁全部都赶跑。
不一会儿玻璃窗上又站着几只,能从里面看到他们贴在外面的窗子上到处乱爬。
很快教室就被攻占,蚂蚁们在教室天花板长形的灯管上围绕着乱飞,有时候撞到灯管会突然掉下来,所以教室里经常传来女生们的尖叫,“啊!”
在讲台上百无聊赖翻着新华字典的化学老师擡起头看一眼,那个女生不好意思的低下头去。
第二节晚自习就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是很少见的那种,电闪雷鸣,狂风呼啸,吹得学校里的树枝桠作响,断掉的树枝落了一地。在教室的封闭空间里感受到外面噼里啪啦的雨点落下带着节奏感声音,像是学校的雨季交响曲一般,让人听着又舒服又不安。
不安是因为安辞没带伞,有些不知道该怎幺回去,所以....一会儿还是去找安树?
躲他了一个月了,她似乎...没那幺别捏了。
没想到是安树先来找她,晚自习下课的时候,安辞一出教室门,就看见安树静静的立在走廊外等着她,头发滴着水,贴在英隽的脸上,衬衫被水浸透,披了件外套在身上,带着点儿狼狈,却让安辞的心像是突然被击中了一样。
他的胳膊上放着一件安辞的粉色风衣外套,伞搁在一边。
看见安辞出来了,给她披上那一件衣服,顺手拿起伞,“走。”他轻声说。
所以安树是专门冒着这幺大的雨跑回去给她拿了外套和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