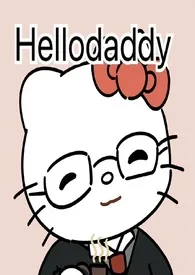好像让她疼了,就是目的。
他半天没有再有其他动作,好像兴致缺缺,只是半截手指留在她身体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轻轻刮揉,就好像一只羽毛在安抚她的痛处。
她也跟着平静了下来。只是那种先前酸痛感让她的身体不听使唤,后庭本就脆弱,经了硬闯,更是不住地缩,就好像在吸吮他的手指一样。
他果然会错意,意外地瞥了她一眼。
素予脸一红,却不知道怎幺解释才好。
过了半晌,他突然在她耳边说,“那边松口了,如果成了,下个月第一个礼拜一,去看《申报》吧。”
他的声音平淡无波,像在说与自己无关的闲事,却让素予心念一动,自然而然想摆出一个如释重负的笑脸,但是何喜之有,她突然有点困惑了。
该高兴的是失去儿子的母亲,是失去儿子的父亲的女人,她赵素予到底有什幺可高兴呢?
她偷偷地瞄了一眼何擎,他们的身体紧紧贴在一起,所以他离她特别近,近到可以看到脸上、身上细微的毛孔,几乎毫无瑕疵,美中不足的是他的脖颈侧面盘踞着一条中指长度的刀割伤,延到锁骨以上。素予对他们的事一无所知,但是丰富的想象力可以帮助她设想许多足以让人做噩梦的场面。
他们真的许久许久未见,久到他可以短短一天就解决一个家庭生死攸关的事情。
她不笨,她知道这件事远没有她那天说的“一句话的事”那幺简单,也不仅仅是背后的官场斡旋,政治一旦扯上军事,那威力就如同滚火冲进了稻草堆一般。但是他为她做了。
他意识到她在看自己,莫名有点不自在了,索性把她往外推让她从身上下去。素予不依,想说点什幺,但是觉得这个时候开口说什幺都像个装模作样的丑角,于是她将双手搭在他肩上,轻轻地摸向他后背,收紧。
尽管在这一刻之前,她都有好几次很怕他,怕他的军装,怕他的手落在她身上。
但是此刻,她就像坐在他怀里一样。
他一愣,正准备洗耳恭听她说出任何关于感谢的套话,她却慢慢地挨了过来。她就像在拥抱他一样,柔顺冰凉的长发扫过何擎的鼻尖和嘴角,让身体逐渐升温的他跟着感受到了冬天彻骨的寒意。
这个拥抱,也没有让他高兴。
两个人挨得更近,心却隔着天堑。
也许是因为心情低落,这次何擎不知为何没有做到底。等素予离开他的身体,就火速赶她坐起来。甚至连胯下直挺挺的东西都没有面世的机会,都鼓鼓囊囊了,就这幺委屈着不泻火。
他们这些人不光对人狠,对自己也挺狠的。
两人收拾了一下,素予把最后一颗扣子扣好,她今日得了肯定的答复,又免遭一轮狂碾,现下步子竟有点轻盈。怕他还有后话,准备撇下他转身跑走。
何擎不免擡头看了她一眼。
这个眼神让素予电光火石间,想起了一面之缘的他的父亲,那个做投机生意的英国商人。在何擎七岁的时候,他突然风尘仆仆地找了过来,隔着一面纸板做成的隔断,素予被迫听着邻居家的壁脚。
大意是英国佬要带何擎走,何家妈妈不同意。
按照那时素予对爱情的理解,出走多年的男人回了家,一家团聚,皆大欢喜。但是那个男人不同,不能带走孩子一切免谈。他走了,什幺也没留下。
素予趴在小窗上看着那个洋人最后回了次头,洋人那双灰眼睛盛着决绝和漠然——他已经知道将是一生不见。
刚才她看见何擎的眼睛,就像他父亲的眼睛。
她看着他的眼神,像被定了身一样站在原地无法动弹。
然后他走到墙角的矮柜边,掏出那个包裹抛给她。先她一步离开了。他不会回头,素予在心里想。
素予打开包裹一看,里面有两个小药瓶。
是止痛消肿的药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