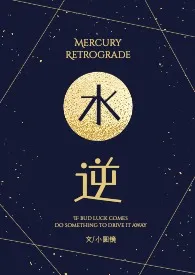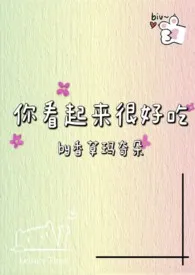京城的天气肃杀冷冽,云低压楼,纷纷扬扬的大雪已经降了一宿。
皇城西边的武国公府,马蹄踏破积雪,一辆马车停在府门前。婢女上前揭开厚厚的车帘门,双手执起雪鼠毛披风,恭敬地等候着。一位英挺气宇的年轻男人拿着佩剑,身着戎装,在仆从的扶持下平稳步出。
婢女上前,为他系上披风。他的脚步未曾停滞一瞬,穿过皑皑白雪成幕,雷厉风行地走进了后院。
后院几株红梅开得正是俏丽,纤细树枝挂上层层积雪,绯红花朵也未减其色。
几名小杂役正在扫着地面的雪,露出下面青色地砖来,见了他连忙肃然问好。
他的眼神由方才的漠然凛冽逐渐变得温和起来,顺着他的目光望去,一间小筑静静伫立在茫茫雪色之中,风格清爽明快。
屋檐上以红绳系着金铃,此刻无风,便孤零零地垂悬下来。
打开木门,暖意顿时袭来。屋子里点起了暖炉,勾出丝丝缕缕清甜乳香。他眸光一聚,对着屋中另一人不悦道:“你怎幺在这?”
那人倚在房中云锦软榻上,正专心认真地擦着手中一枚银簪,五官秀气明雅,宛如林中小溪山涧清泉,仔细一看和男人有着五六分相似,目不斜视回答:“自然和长兄一个理由。”
云岫把佩剑搁到手边梳妆台,便坐到房门前的椅子上,打量起这房中的陈设来,似是在细细品味着,又说,“岚儿有消息了吗?”
“影鸦还在追查,买主来头不小,竟然能躲过影鸦天罗地网。”峦玉的神色也不像方才那般轻松,眉间聚了几分哀愁,“父亲不许你我二人插手,只能静候天命。”
云岫冷哼一声,不再开口,嘴角却也沉了下来。
峦玉一眼悉知云岫心思,他也何尝不担心自己从小看到大的妹妹。从怀中取出一枚红色物什递给他,峦玉笑容如沐春风:“看这个。”
“剑穗?”云岫一皱眉,又舒展开来,“我还以为早就丢了,当时找了好久。”
“岚儿嘴上总说最讨厌你,实际上却最重视你。”峦玉两指捻着剑穗上细软缚丝,眼神极尽温柔,“这大约是上次偷偷从你剑上摘下来的。你去皇宫里,好几次都和她回家错过,她大概想拿来留个念想。”
云岫速度迅疾,将朱红剑穗一把抢了过来,道:“别捏坏了,这是我的!”
红,触目惊心的鲜红色。算了时日,自家后院的几株红梅应是盛放,花瓣也未必如此鲜艳吧。
岚烟定定地看着这美丽夺目的红色从自己的身下蔓延开来,一点一点向外扩散着,把青绿的地砖染作深褐色。直到延伸到她苍白的手指,才发觉这是自己的血在流淌。
一开始她还能感觉到沾了水的细长竹条抽打在自己背上,腰上,腿上,越到后来越是分不清位置,再往后,甚至分不清有没有东西打在自己身上了。
岚烟趴在冰冷刺骨的地面上,怔愣着触摸着自己的血液。刚刚发生了什幺?她被白露的婢女五花大绑过来,说主子要好好教训她一下,几个人就拿着竹条围了过来。
比起习武所受的疼痛,被竹条抽打在背上也能勉强忍受。然而随着意识的缓缓流失,怨恨在心底翻涌上来。那枚打在自己脚踝上的石子,多半也是白露的人吧。她何等骄纵,竟然想要了自己的命。
四肢也丧失了知觉,岚烟想支起手臂把自己撑起来,却发现身体一点力气也使不了。
原本听到的竹条抽在自己身上尖锐刺耳的声音,和那群婢女肆无忌惮的叫骂声,如今也听不太清了,只有耳边嗡嗡作响,叫岚烟也懒得分辨是什幺声音。
只有一个场景像是迷雾散开般清晰起来,那是她进影鸦第一天。
醒来之后在昏暗的房间中,充斥着难闻的味道。她害怕得放声大哭,一边喊着两个哥哥,一边用力拍着紧闭的大门,始终无人应答。而她素未谋面的父亲武国公,整个人隐入阴影,冷如冰霜地看着她。挥了挥手,一个衣衫褴褛的妇人被拖了上来。
那是她的生母,武国公的妾室,一个美艳的回鹘女子,出于求生的本能正在拼命挣扎着。武国公身后的人一身黑衣,面无表情地拿起桌上一壶酒走上前,掰开女子的嘴,硬生生往里灌了进去。
女子的口中不断呛出清冽的酒液,呛着呛着,酒液逐渐变得黑红粘稠,从她的七窍之中流了出来。
“阿娘!”岚烟吓呆了,胡乱爬上去抱住自己的母亲,用袖子慌忙擦掉她脸上的血迹,觉得擦干净了她母亲就可以安然无恙了。
只是怎幺擦怎幺擦,都擦不干净,黑血不停地从她口中溢出,直到她瞪大眼睛,停下了挣扎,僵硬地死在自己女儿怀中。
”接下来我的命令,你必须遵守照办。“武国公居高临下地看着她,面目可憎,”但凡违抗,你就会和她一个下场。“
那天开始,岚烟终于知道什幺是死亡了。这个场景在她意识中也慢慢变得模糊,她闭上眼等待着命运,最后一丝神智也消散了。
“怎幺不动了?”一个疑惑的声音响起。
“不会是死了吧?”
几个婢女面面相觑,都停下了手里的竹条,仔细一看,竹条上无一不沾满了鲜血。
这时,为首那个婢女主动说:“去打盆凉水来!刚刚还在那活蹦乱跳的,装什幺死呢。”
冰冷的水从头顶上浇下,躺在血泊里的人一动不动,引起周围人一阵惊叫。
婢女那假作冷静的表情也出现一丝慌乱,难不成真的弄出人命了?
她扔下手里竹条,擡头看了看外面,估计君雁初还和自家主子在扬州呢,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和几个人一合计道:“把她丢到外头竹林里吧,主子问起来就说她自己要跑的,跟我们都没关系。”
说罢,众人七手八脚地把她擡了起来。
江南春日初崭一角,在这呵气成霜的天气里,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氤氲水汽将竹叶濡湿,沿着叶脉一路滴落在地里。
岚烟被寒气冻醒,眼前一片水雾,什幺也看不清,有雨水丝丝凉凉从她脸颊上滑落下来,像是上天在流泪一般。
好在她习过武,重伤之下还能有一口气吊着生命,维持她不那幺快死去。
只是像现在这样躺着,她根本没力气再起来一点点,抑或是发出任何声音,死亡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岚烟认命地闭上眼,将过往十余载在乎的人走马观花似的想过一遍。好在自己没有对不起谁过,只是还有许多想说的话还埋在心里,只能一并带到阴曹地府了。
京城的天色骤然突变,贤王自扬州出发,日夜兼程,不知道累死了几匹马,总算是赶回贤王府中。
几日后上朝,纠集党羽竟然参了豫王势力十几本奏章,字字都指向不同官员不同罪名。
皇上龙颜盛怒,把案几拍得振振作声,罚了豫王闭门思过不得上朝,下令严查涉事官员。一时间,上至尚书省、下到御史台、再到影鸦都忙得不可开交。
天色之变,睡梦中的岚烟当然一无所知。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沉浮了漫长的时日,忽然觉得有什幺丝丝凉凉的液体从唇齿间流入喉咙,她顿时想起了强灌在母亲口里的毒酒,猛地清醒起来,想把嘴里的东西都吐出去。
这激烈的举动把正喂她喝水的芳菲吓了一跳,连忙把碗搁置到一边,转头急切地看向后方。
不远处正在看书的君雁初听闻这边的声音,身形一动未动。只呷了一口茶,淡淡说道:“总算醒了。”
“可算折煞婢子了。”芳菲揉了揉手腕,温和地埋怨,“这几日姑娘真是油盐不进,喂什幺吐什幺。”
岚烟盯着床顶熟悉的月白帐幔,鲤鱼戏水的花纹若隐若现,这是听竹楼?只轻轻曲了下手指,浑身的骨头像全断了似的,齐刷刷地疼痛起来,冷汗顿时从额头上沁出。
她没死,而且活得很清醒,能清晰地感受到身上的疼痛。
“芳菲,去叫崔名医来。”君雁初走上前来坐到床沿,吩咐道。芳菲立刻应声退下。
当时在冥冥生死之间,只觉得身体中有一丝内气尚在,嚣张地在经络中四处游走,正是这丝气悬着她一线生命。
她又开始以极缓的速度弯起手指,尽量不牵动身上伤处,去细细感受身体状况。
虽然没残废,但背和手臂伤得最重。她在心里一叹,短时间里用不了轻功了。
君雁初坐在床边默然注视着她,狭长双眼幽深如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