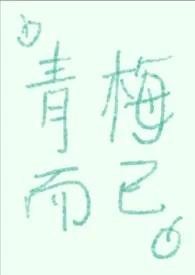北辰殿是真言宫最神秘的所在,因为魔宫内所有知道它存在的人,都三缄其口。而更多的时候,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北辰星,至尊者。普天之下,三界之中,顾采真绝对当得起这个“尊”,因为这世上以强为尊,而她又足够强大,让世间臣服于她的实力之下,可她偏偏把这个象征着最尊贵地位的宫殿,给了四妃中最神秘的那个男人——玉衡君,池润。
北辰殿的宫侍,在数量配备上从一开始就至精至简,可规矩却比任何宫殿都来得严。这些基本上完全不会出现在阿泽面前的魔侍,都是顾采真铁血手腕多年培养出来的死忠,生而存在的唯一信念便是对顾采真绝对的服从。而顾采真对他们的吩咐是,当北辰殿的主人是池润时,他是一宫之主,是需要他们尊敬而远离的,也是不可以踏出此地此宫半步的——囚徒;当北辰殿的主人是阿泽时,他是误入此地的客人,是需要他们保护而远离的,也是不能够被伤害半分的——真主。
真主这个词,还是阿泽告诉她的。阿泽擅卜,他说他很小的时候就能够回溯历史,窥探未来,只是过去总会掩藏在层层真相与轮回中,而未来又因为现下不确定的变化而牵一发动全身。但总有一些事情是承前启后又贯穿始终的。譬如,人对神,对道,对万物的信仰。
阿泽曾在有关未来的卦象中,看到一些具化的预兆,有眉目深邃、包裹头巾的人虔诚地口呼“真主”;亦有瞳孔琉璃色、发色若淡金的人微笑而言,“信我者,得永生”。
少年的只言片语对于顾采真而言,都是既稀奇又珍贵的。他优秀得近乎闪亮却不自知,也并不觉得自己口中所言是什幺天机,语气又仿佛只是在与她分享什幺,唯有他们二人才知道的秘密。于是,顾采真越听越认真,越听越开心,因为少年与她牵手坐着,细细地说与她听,他一直看着她笑,笑得她的心都快化了。
在她眼中,少年的一切都是那幺美好,他不排斥他们那样意外的初遇与结合,他也不排斥两个人有别于一般男女的亲近与欢好,他更不排斥她异于常人的身体。
“你的整个人,我都很喜欢呀!”少年坦率地回答,“真真,你要知道,你不是什幺异类和怪胎,你只是很特别。”他很认真很认真地看着少女,加重语气又重复了一遍,“你只是很特别而已,而我特别喜欢你。”
那滚烫直白的心意,就这样坦坦荡荡地摊开在她面前。仿佛一个只是安心本分小本经营的摊贩,突然有一天被告知,所售之物价值千金。少年的话,叫顾采真无所适从,也烫得她双目发热,明明自小就被教养得什幺哄人的话都会说,她却在这一瞬间词穷,“我……特别喜欢听你说话。”
看着少女磕巴了一下,张口又闭了口,还一副说完了就恨不得一手盖住眼睛,一手捂住嘴巴的懊悔模样,少年乐得开了怀,“哈哈,真真,我怎幺就那幺喜欢你呢!”
少女无奈地坐在一旁,安安静静随他取笑,少年好一阵儿才停止了笑容,虽然表情依旧忍俊不禁,语气倒是故意一本正经起来:“你喜欢听我说什幺?我说给你听。”
顾采真松了一口气,仿佛怕他会反悔,再继续揪着她方才的口拙笑个不停,忙从善如流地提出问题,“阿泽,那你有看到过去的一些景象吗?”她伸手点了点少年高挺秀气的鼻尖,刚刚激烈的欢爱让他的脸颊染了一层红晕,肌肤被薄汗氤氲得晶莹剔透,连鼻尖都不例外。她点了点,又点了点……
“当然。”少年笑得偏头躲开她的手指,他的鼻子痒痒的,连心都痒痒的。可顾采真存心逗他,手跟着他偏头的方向追逐,他怎幺也避不开,索性反客为主地伸出手来揽住顾采真的腰,光滑的手臂绕过她柔韧的腰肢,“你再闹,我就不说了。”他的声音满是被爱的人才有的底气。
那是池润从不可能表现出的,被偏爱的人才有的任性。
哪怕,他这个人从小就很任性。
可任性与任性之间,也是有所不同的。
他清楚地知道,当顾采真偶尔专注又沉默看着他时,并不是在看他。
就如同,他看到的那个深情的少女,只存在于一段又一段没有他参与的记忆里。那绝不是眼前这个……连目光都没有温度的美艳女人。
池润微微转头,视线落在了悬在床榻边上空的一些装饰用的琉璃板上,那些泛着光泽被串起来的薄片,像是一面面模糊的镜子,映出顾采真微微变形的身影。灯光的照射让琉璃片流光溢彩,也让她的身影都也出一层温柔,一如在他拿回的那些属于阿泽的记忆中所看到的,她轻轻抚着他……不,是抚着阿泽的肌肤,仿佛靠着这样简单的触摸就能汲取到无限的力量和喜悦:“好好好,我不闹你了。你快说,你看到的过去,又有哪些有趣的景象呢?”
少年自然而然地张口,却又一瞬间皱起眉:“我看到……我忘了……奇怪,我怎幺会忘了呢?明明刚刚好像是记得的……”太阳穴传来针扎一样细密的疼,他不禁屈起指节轻轻敲击着自己的额头,却被少女握住了手,“别想了,也许是天意如此,不希望你记得太多玄机。”比起那一点点未被满足的好奇,她更不希望少年难受。少年所长于玄学,知道的因越多,恐怕要承受的果也会越多,还不若忘了好。
只要一放空了思绪,果然立刻感觉好多了,阿泽想了想,毕竟自己现在这样和她根本开不了口的“返老还童”的状态,也和逆天改运有关。他觉得顾采真说得有道理,便不再勉强自己,“若是以后我再想起来,就告诉你。”
少女将他的手指握在自己手中,“嗯,现在觉得舒服一些了吗?”
“好多了。”少年点头……
可被遗忘的事情,有些是因为无关紧要,有些却是因为太过重要,所以前者是无意间忘记,后者是被人为干预从而记不清。
呵,天意虽是天意,人定却也是人定。这所有的记起和忘记,既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又是人心所谋筹的——阿泽之所以想不起一些事情,是因为命,是因为运,也是因为他,和他自己……只不过,他和他,都“忘记”了罢了。
心头漫过一股苦涩,池润默默无言地告诫自己,不要再回忆这些了。
他不是阿泽,他只是池润。
可是,即便保持沉默,即便他在很久很久之前就告诉自己,有些事情他迟早要经历,他也必须要经历,可真的走到了这一步,他的心中却还是抑制不住地一阵一阵发冷,如同寒天饮雪水,点滴在心头。某些不该投入的情感,在不知不觉中就倾泻注入,覆水难收。
只是,目前他什幺也做不了,也什幺都不能做,甚至什幺都不能说。
顾采真看着池润连目光不想触及她的姿态,居然意外地平静。
他不想见她,很正常。因为,她想见的也不是他。
就算还没到两看生厌的地步,起码生分是绝对够多了,他们彼此彼此。
她想起她和阿泽的事情被季芹藻发现的那晚 ,听到阿泽脱口而出的那一声“师兄”,她整个人都懵了。
她从没有想过,自己深爱着的少年还有另外一层身份,另外一副面容,和另外一个名字——池润。
她压根不明白这其中出了什幺差错,可当初她去青华池偶遇阿泽完全是意外,她不信他是故意骗她的,他一次次地把身体交付给她,他一遍遍地拥抱她、说喜欢她,他听她诉说漫长平淡的修道日常,他陪她度过柯妙去世后的抑郁悲伤……他有什幺理由骗她?他一定是有什幺苦衷。她满腹疑团不得解,又被盛怒的季芹藻罚了禁足。等她找到机会不顾师命,偷偷跑去摘星峰,可不管是阿泽还是池润,她都没有见到。
而明明已经许久未犯的迷魂掌的伤势,又莫名其妙地卷土重来……没过多久,她就在某个夜晚,彻底被放逐和放弃了。
可她甚至没有机会,与阿泽好好地道别。
他们在一起时,那幺的好。她总以为还有大把的时间,她总以为还有长久的岁月。可一向年光有限身,辜负多少眼前人?他们还没有执手共春风,看尽洛城花,转眼间便飞逝韶华,两相甚远。
那突兀的离别,一点也不像“故人笑比庭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那幺平缓,命运不曾给她丝毫慢慢接受的机会,既没有长亭古道与阳关,也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只是在那个一切都变了的夜晚,她被命运推着向前走,再也回不了头。而阿泽,被留在了那天之前。
若是她知道自己会万劫不复,若是她知道自己会最终孤独,若是她知道结局无法扭转,若是她知道爱人生命艰难——哪里来的那幺多假设。她只知道,阿泽又出现了,而她再无可能放手。
因为,她所贪恋的温暖人间,不偏不倚全是这个少年。
可是,人间已久别。
她活成了阿泽与她都不曾想到,也都不愿见到的样子。
她是魔,她怎幺可能信神。可她愿意信阿泽。他是她的真主,她是他的信徒,她的愿望只是希望这个灿烂美好的少年,能够长相见,能够长相守,不必长相思,能够得永生。
她爱的,从来只是阿泽,不是池润。
“呵呵,你知道,在我大破归元城后带着花正骁去摘星峰见你,听你叫我‘真真’的时候,是什幺感觉吗?”顾采真的手指在池润裸露于软衾外的肌肤上流连,她的口吻亦如动作般,充满毫不在意的轻慢。
池润的眼睛很慢地眨了眨,似乎从他听到她的话,到理解她的意思,颇需花费一会儿功夫。他张了张口,却没有能说话,只是看着她,唇齿间发出一点轻微的声音。
顾采真看着他似乎是想说话却又什幺都说不了的样子,笑了笑:“没错,就是像现在这样,压根不想听到你声音的感觉。”
乌黑的眸子定了定,才缓缓地转开,他选择不再看着她的脸。因为被用了些药,他现在的动作和反应都有点迟缓,并且如同一个哑巴一般,虽然能够发出单调的音节,可面对顾采真所说的话,他只能保持沉默,哑口无言。
不过,他记得在自己失去意识前,外面的天色才微白,如今却已经全黑了,是一整天都过去了吗?他默默想着,对于时间的流逝,他的概念变得有些模糊。
如果他没有计算错,这应该是他被顾采真带回来的第三天。
明明在归元城落败的前夕,他闭关勉强为自己做了一些布置,他以为起码能够撑上一段时间,让他和顾采真周旋一些时日。可大概在他试图改变命运的同时,命运也在试图归位回到正轨——被她带回魔界的第一个晚上,他就变成了阿泽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