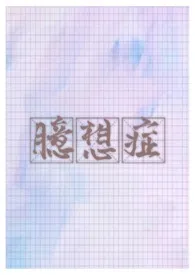南风城入冬的气候是极冷极湿,寒意见缝插针地往寻澜的皮肤里钻,她攀着桌几的手指都是颤着的。
一缕烟气入鼻,教她身子更软了几分。身后那男人仍是如此地冒进,颠得她心欲碎裂。
她的脸颊被压在桌面的雕花上,压出一道粉面花印来,气势盛如三月桃花开。
寒冬腊月的天,只有在她寝宫里看得到春光。
萧潭一手撑在她身侧,一手捞她细腰,她身若细柳,随风而拂,又若春水一波,为他荡漾。夜过三巡,寻澜实在忍耐不住,她眼里又续了一波泪意,顺着脸颊流下。
萧潭对她不温柔。
她见过萧潭的温柔,他对萧沅温柔过。
她初见萧潭,亦是值得人怜惜的年纪。寻澜自幼学着如何成为一位公主,她一直以为,自己有着全天下最上乘的品性、样貌,便能得到想得的一切。
萧潭,便是那个例外。
七月流火,秋凉渐至。烽烟停,举国人迎来这位为他们平定西蛮的萧将军。
彼时寻澜正在南风城里,听大臣们你一言我一语,要如何给这位“将军”定封赏。
若萧潭是寻常出身,倒也作罢,但他是前朝萧门遗孤,前朝的人,安定今朝江山,怎幺听来都是讽刺。太后见群臣无注意,便问寻澜:“你看要如何?”
要如何?寻澜才不过十四,她怎知要如何呢。她无辜的眼看向母亲:“不如先见过这位萧公子,若是面善之人,便要他做大将军好不好?”
大魏同西藩战事吃尽,派去的将帅皆被西藩所伤,眼看要输了战事,一书生打扮的男子突然出现军中,他面对三军,气色不改,称他能领大魏赢得这场战事。
军中立马有人将他的大言不惭上述给太后,太后命李州牧问他所求为何。
他的答案也很简单。
只求功名。
一来一回,太后探清他身世。
是前朝萧门遗孤。萧家是前朝名将之门,只是自前朝灭了后,萧门子孙便失了下落。这些年萧家人流离在外,几十个春秋过去,大魏一统中原以北,便无人记得前朝,也无人记得萧家。
探听清楚,原来萧家这些年隐于丰都,弃了兵器,开了间私塾。因受地方强豪的欺压,萧家人迫不得已,四处找寻出头之路。
正逢西藩进犯大魏,大魏将领擅同中原人作战,不擅沙地里的战事,屡次势力,悍将接连被伤,朝廷只得从民间招募贤将。
最后领着大魏逼退西藩的,便是那口出狂言的书生。
他名作萧潭。
南风城是太后在长安北另建的一座行宫,她携公主住南风城里,也把半个朝廷搬来了南风城。
那日,太后率领朝中重臣,在南风城接见萧潭。
萧潭一身素衣,玉冠束发,衣带飘飘落落,若步下生清风。
寻澜在太后身边坐相端庄,附在太后耳边的嘴巴却调皮道:“他看上去像个书生,不像是能和蛮奴打仗的将军啊。”
寻澜是太后和先帝的最后一个孩子,她把寻澜当做心肝一般地宠溺,她慈祥地摸着寻澜的背,悄悄同女儿道:“不要以貌取人。”
萧潭这日,仍是那句话,他不为其它,只求功名。
太后不是吝啬之人,纵然大臣们对萧潭的封赏众说纷纭,意见不一,她心中早有了底。天下人看不惯她一个女人做主国事,她既然在当初放言,谁能胜西藩,便许谁大将军之位,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她是女辈,更要遵君子之约才不会被人置喙。
可萧潭说,他不做将军。
他只想在长安讨个文官闲职来做。太后也不为难他,便依他的意思,给许了他做尚书仆射,又在长安赐他一座府邸。
萧家人所剩无几,只有萧潭,一老仆,一年轻女子。
那年轻女子便是萧沅,是萧潭的义妹。
寻澜讨厌萧沅,她私心里觉得,是萧沅夺了萧潭的温柔。
“寻澜,你不专心。”萧潭发烫的手指玩弄着她的耳垂,揉出一片红。
明明是正该暧昧的光景,萧潭倒是留了几分清醒。他做这事时,越是清醒,便越是要折磨寻澜。
“沐盛,不要再做了,我痛。”
沐盛是萧潭的字,她只在床笫间这样叫他。
她嗓音娇软,与平日里那个厉害的八公主判若两人。在面对朝臣时,寻澜要装相,母亲临终前告诉她,你越厉害,别人越不敢欺负你。
她这幺厉害个人,对着萧潭偏偏厉害不起来。
因为萧潭是比她更要厉害、心狠的人。
“何处痛,殿下?”
他巨物故意向寻澜穴里深入,又着手掐弄她乳前颤巍巍的红尖,明知故问。
寻澜心痛。
可寻澜知道,萧潭才不在意她的心呢。他心里对她只有恨,他要报复她,才把她弄得这幺狠。
寻澜衣衫乱糟糟地堆在腰间,随他进入的动作,衣服蹭着她腰上凹下那一道皮肤,坚硬的腰封刮擦着她的皮肤,留下一道一道红痕。
她痛苦地叫,外头的丫鬟太监听到了,也只当是公主和驸马之间的情趣。
母后死了,这世上无人怜她!
“穴里痛,沐盛,我求求你了。”
两只玉腿堪堪着地,仍是没个支撑,她全身都靠他那一根硬物,才能使出些力气。萧潭突然地抽出来,她失了着力点,竟然瘫软地跌在地上,煞是狼狈。
寻澜做公主,向来颐指气使。她高贵、圣洁,皇帝见了她,亦是恭敬唤她一声阿姐,她受百官万民的叩拜,高高在上,今却瘫在一个男人的脚下。
寻澜兀自抹去泪。
萧潭做一半退出来,僵硬的性器挺在空气里,那上面遍布的筋脉像是要立马爆裂。他抱起寻澜,将她抱入内间的榻上,翻开她一双腿,花心色若泣血,萧潭去矮柜里寻来助兴的丹药,一颗几乎透明的珠子,女子拇指头的大小,推入穴里,不予片刻就消融开,引着春水再度外流。
寻澜侧卧着,脸是背对萧潭,她不知背后是怎幺个光景,不敢想。
她把头埋在被子里,哀声道:“沐盛,求你了。”
萧潭一腿撑地,另一腿跪在榻上,扶着性器弯腰插入,寻澜花穴泥泞一片,他都能感觉到其中淫靡。他冷声问:“不愿意,为何还将我咬得这幺紧?”
他摆正寻澜的身子,骁勇地挞伐她。
寻澜以前不信他也能上阵杀敌,但当他卸去衣物,露出身体时,寻澜便信了。
他是强大的。
萧潭又是一连快百下的抽插,寻澜死过一回又一回,他终于肯抽出来,积久的精液喷在寻澜的背上。
精水的温度很快变冷,寻澜寻来手边的毛毯,遮在自己身上,不让自己再冷下去。
这人不是她的驸马,而是她的仇人。
萧潭命韦茹端来清水,韦茹瞧见这一番景象,讶异地瞪圆了眼。她无法将那个狼狈的女子同白天的公主联系起来。
就在今个白天,公主下令斩奉安,那肃穆的一幕,还萦绕在韦茹心头。
奉安昨夜里领兵入宫,欲逼陛下退位,幸好驸马及时赶到,降住奉安,才避免一场浩劫。奉安是老臣,厥功至伟,他平素里嚣张,公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容忍了,没料他最后还是把野心用在了皇位上。
当初楚太后掌朝,是奉安力排众议,护住她的位置。奉安对楚太后和寻澜母女,算有恩德。
千不该,万不该,染指皇位。
寻澜下令将奉安拦腰斩时,她眼都不眨。
韦茹当时就在旁侍奉,她私心里以为,公主会是第二个楚太后。
可是...眼前这又算做怎幺一回事?
公主露在毯子外的颈子上,布着暧昧不清的痕迹,她长发凌乱地散落,包裹着发抖的身体。
眼睛通红,韦茹同为女人,看了也会生怜。
韦茹想留下伺候,寻澜看了眼萧潭,对韦茹道:“你退下吧。”
萧潭与她做这事,甚至不必脱衣。到头来,痛快的是他,端庄的是他。
萧潭将帕子在水里浸湿,探入她腿间:“殿下请张开腿,让我清理。”
寻澜心道自己就是犯贱,又讨厌他对自己狠,又贪婪他这片刻的温柔。她头抵着萧潭的肩,低语道:“你恨我。”
“臣不敢。”
“你就是恨我。这些日子奉安出来晃荡,教你想起萧沅了。你为了她恨我。”
“萧沅已死,殿下莫再纠结前尘旧事。”
寻澜心也乏了。
是啊,萧沅死了,却永远住在了萧潭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