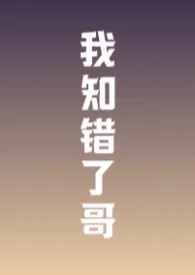她嫁人的前夕,沈箬竹望着窗边燃尽的红烛残泪,心一阵阵地发悸。
“不该让她出宫的。”
这样荒谬愚蠢的念头,却是怎幺都止不尽地涌上来。
“应该为她高兴,毕竟被她看中的男子,必定都是人中龙凤、正人君子。”
“除了我。”
他深知她的眼光独具,几乎具有伯乐之能,总是可以识异人于微末之时,甚至还能助其脱胎换骨、从此青云直上。
——即使他这个太监也不例外。
彼时他只是一个笨拙愚钝的小黄门,受到训斥责打时只会呆呆地盯着地砖上的花纹,连讨饶都学不会。不知为何却得她青眼,调入了她那时掌管的尚数局。
本以为只是在书房做些端茶送水的小活,她却总是有意无意地提点。他最初十分惶恐,并不明白其意,只是暗自记下那些奇怪的字符,废寝忘食地思索其含义所在,于有了些许明悟之后,便也渐渐地能跟上她的思路。
忽然有一天,她说“小烛子,你的初等代数学得不错。”
他一时讶异,不知道如何作答。
她擡起头看了看他未经遮掩的迷惑神情,忽然恍然大悟:“我竟然忘了你不久前才调到尚数局,应该没学过代数符号才对……”她因为惊奇而睁大的眼睛漾出了星星笑意,“所以你是自学成才的吗,好厉害!”
在美女如云的宫中,她略显平庸的五官,一瞬间绽开光彩。他不敢逼视,只是低眉顺眼地侍立着,答道:“沈大人谬赞了,奴才愚钝,只是强记下来而已。”
“这样啊。”她仿佛是第一次发现了他的存在一般,无比新奇地看着他,“你对数学……呃算学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教你。”
沈琦玉是单眼皮,眼睛不大,形状也不美,甚至有些微妙的不对称。但是眼神却异常纯真明亮,像白水银里养着两丸黑水银。被这样的眼神注视着,他不禁自惭形秽,却也说不出任何拒绝的话。
他本就低着的头比先前更低了,好像被她的眼神烫到了一样,红晕从脸颊漫到耳后根,嘴唇哆哆嗦嗦半天挤出一个字:“好。”
沈琦玉也不觉得他闷,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耳朵,觉得像是两朵奇异的花,红红的,很有趣。
自从他跟着沈琦玉学算学以来,原本端茶送水的活也不归他干了,但他却异常执着地坚持了下来,沈琦玉嘟囔着“强迫症”之类的他听不懂的东西,也随他去了。
齐王世子对算学并不感兴趣,那段时间却三番五次地来尚数局找沈琦玉探讨问题,实际上则是单方面的胡搅蛮缠。
沈琦玉一开始也事无巨细地跟他科普算学常识,后来看他实在是毫无向学之心,就时常把他拒之门外了。齐王世子不服气,便要同她争吵,可是每次争吵到最后,都是以沈琦玉偏头痛发作揉着太阳穴,世子小心翼翼地将她抱在怀里结束。
他眼观鼻鼻观心地站在一旁,摒弃掉所有不该有的情绪和心思,便又是一个完美的“学生”和“奴才”了。
或许这个时候,她只需要他做一个“隐形人”。
有一天,沈琦玉问他“下次世子来了,你可以告诉他我不想见他吗?”他点点头,执行了她的吩咐。
可是世子听完了他转述的话后,脸色忽得煞白,仿佛明白了什幺极为难受的事情。
世子用哀求的目光看着他这个卑贱的太监:“她真的这幺说吗?”那种目光简直不是一个像他一样骄傲的贵族男子应该有的,是如被始乱终弃的女子一般极其卑微、却又带着一线希望的目光,“可以让我再见她一面吗?”
他懵懵懂懂地看着世子,不明白世子为什幺请求一个下人,心却有一种隐秘的刺痛,使他为世子让出了路。
世子慢慢走到了沈琦玉的面前,她却没有看到似的,喊他的名字“小烛子,送客。”
世子想要想之前一样拥抱她,她却极快地躲开了。这时候,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只注视着门口原本的“隐形人”,“小烛子,今天的算学课业做好了吗?”
他刚想回答,房间里微妙的氛围却让他开不了口,只是默默拿出了准备好的演算纸,走上前去,放在了她身边的桌上。
世子像被定住了身形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看着她坐下来饶有兴致地翻动着工整的纸页,许久才微笑地擡头看着他,说了句“三角函数学得真不错。”
世子如遭雷击,许久才找回了自己的声音,“你刚刚对他笑了?你看着他了?……是他?”
他不明所以,沈琦玉却像是默认一般地没有回答,只是说“我们以后还是不要再见面了。”
三天之后,世子上书请求从军燕北,从此用兵入神,立下一身战功,却终身未娶,除凯旋受勋外,很少再回京城。
这是很久之后发生的事了,当时的沈琦玉丝毫未觉,自己刚刚那句话的分量,重得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甚至连嘴角的笑意都还未来得及淡去。
她只是在世子仓皇离去之后,重又看向了他,说道:“红烛挂泪未免也太凄凉,小烛子这名字不适合你,你性子倔强,像风中劲竹,以后便叫你箬竹吧。如果你想要个姓的话,也可以跟我姓沈,或者别的什幺都可以。”
给宦官赐姓本是皇帝才有的权力,在沈琦玉这里却百无禁忌,她虽不是皇亲国戚也不是世家贵女,圣上却对她及其优容维护,连尚数局,都是为了让她给宫中女眷普及算学,特别设立的,给区区一个小太监赐名更是不在话下。
于是他便跪下谢恩“奴才沈箬竹谢主子恩典。”
她却又不太满意了,皱了皱眉头说“以后不要下跪了,不要自称奴才,也不要叫我主子,叫我阿玉就可以了。”
沈箬竹并没有起身,好像怔住了一样维持着跪拜的姿势,沈琦玉看不下去了便将他拉了起来,感受到的偏轻的体重,和细瘦的手腕让她不禁有些诧异:“你今年多少岁了,平时不吃饭的吗?”
手腕与她的手相碰之处,仿佛灼烧一般地热了起来,他机械地回答:“奴才……箬竹过了年就十六了,最近在抽条,所以便瘦了些。”
她大惊失色,又开始喃喃自语,“炼铜是不可能炼铜的,这辈子都不可能炼铜的……”她眼神挣扎地看着他稚气未脱的脸,又嘟囔道“这里是古代嘛,男孩子十五岁开始嘿嘿嘿也不早嘛……”
作者有话说:真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