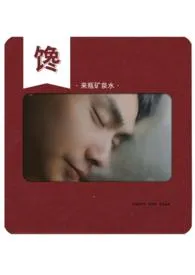黎⽣今儿个是起的有些晚了,倒也没有人催她,都知道她被习先生包了,连从前隔三差五骂她晦⽓的妈妈都变得客⽓起来。
随脚踩着绣花拖鞋边⾛边撩了衣服,拿过那淡粉色旗袍⼀看,竟不知几时划了个⼝子,她⼼下⼀想,坏了,赶紧又把睡衣套了回去,翻出针线开始缝补,就怕那习先生逮着这个那个的由头⼜算她⼀笔。
他总有⼀千万种理由惩罚她,手段不一,样样高明。本就是个浪荡⼦先生。
黎生还在乡下的时候曾听说过“先生”这种称呼,当时只觉得是清雅⼜高贵,整个村⼦也就学堂里的张先⽣能得如此尊称,却不想到了这⼤上海,混社会的竟也能叫“先生”。
为此习先⽣还抱怨,他惯不爱这种文绉绉的玩意⼉,可惜上头发话了,捞偏⻔的也要把纪律和文化搞起来,切勿让⼈小瞧了去。
习先生对此十分不屑,⼿叉腰说,地痞流氓穿上西装那也是穿着西装的地痞流氓!她被他的神态逗得咯咯咯笑。
要说这习先⽣也并⾮什幺⼤人物,最多勉强算上头的六七把手,偏这个妓院归他巡,⼀个⽉来那幺几回,也足够保她在这过上稍安稳的日⼦。否则,照她这种条件,定是要和几个姐妹挤在大房的。
指尖握着针线翻飞,三两下便补好了,原本的⼝子被⼀只蝴蝶盖过,倒显得更灵动。她换上,描眉画唇,⼜抹了层他新送的雪花膏,鹅蛋的⼩脸便立刻精神起来。
早晨的园⼦⼈不多,除却几个喝喝花酒的散客,多半是来抽大烟的,一人握⼀烟枪子,⼗十三四的丫头一旁轮流伺候着,有钱些的便开
个包房,约几个烟友一同聚,伺候的女⼦也可挑。
但这不是最高级的。后头那栋红房子,才是真正的富丽堂皇、⾦雕玉砌。以黎⽣的资质,她是进不去的,听说那里边,伺候的可都是大人物,连专⻔开电梯的都是白俄罗斯⼥人。上头那位偶尔来光顾⾃家生意,她远远瞧⻅过一回,约莫很高,但瘦,着⼀身⿊色⻓布衫, 不不像⼲那些的,倒像⽂人做派。
远远跟在后头的便是习先生, 说⽩了是个打杂佬,伺候完了主子,得了闲空便溜到前院找她。
前⼏日他说今晚会来,她打算去铺⼦里买⼏几壶他喜欢的桂花酿, 迎⾯一个刚抽过烟的男⼈走过来, 嘴边⼝水还流着,擡⼿往她脸摸,她躲过,甩甩帕子,娇俏地换了声“爷,您可看路”,躲过去便出了门。
绕过几个拐角,出了这纸醉⾦迷的街,外头和那处泾渭分明,到处是乞丐,穿着开裆裤的孩童⾚着脚到处跑,浑身脏兮兮。
现世道,有⼈饭都吃不上,也有⼤把的人挥金如⼟,艰难说到底只对穷苦⼈而言。